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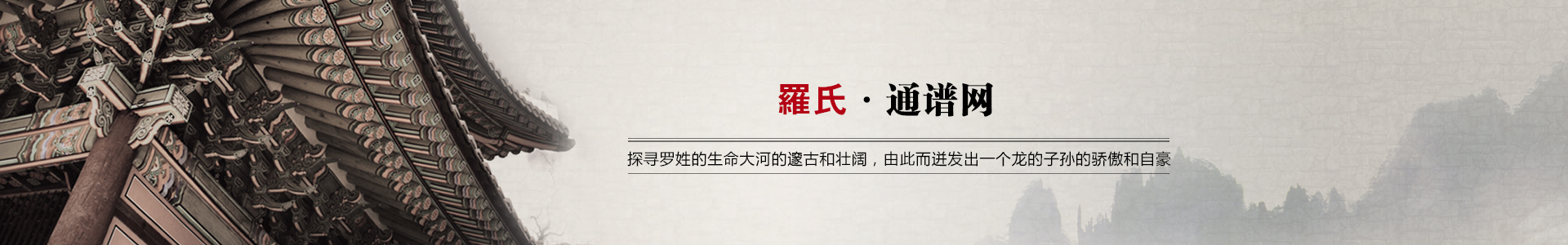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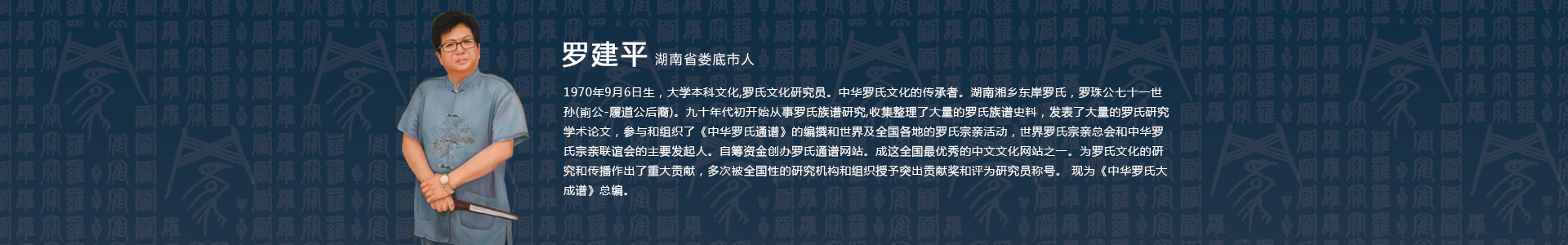
族谱 历史 权力
刘晓春 发布时间:2003-08-23
对于客家人来说,族谱并不陌生。在读中学的时候,我的叔叔就很神秘地把我带到他家的阁楼,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陈旧的柜子,满满的一柜全是线装书。他告诉我,这是我们这一族的族谱,“文革”期间作为破“四旧”的对象,没收在大队部,在某个深更半夜,叔叔又与同宗的大队书记两人合谋将族谱抬回家中藏了起来。叔叔颇为自豪地介绍着族谱中记载的本族历史人物,慨叹家族的没落,已很难找到可以在族谱中“流芳百世”的后人,与临近的其他家族也很难抗衡,还一再勉励我好好读书。那时候,我只觉得这族谱似乎对于我们家族很重要,但我还不能明白与我究竟有多大关系?直到后来,远离故土,漂泊异乡,自己也就慢慢地意识到族谱赋予我一种历史感,无论走到哪里,似乎都脱离不了那一份血缘的牵挂与乡土情怀。十几年后,当我在田野工作中阅读他人族谱的时候,获得的却是更多不同的感受。
1996-1998年间,我曾多次深入到江西宁都县的一个客家村落(取学名富东村)进行田野调查。这是一个有4000多人口的大村落,居住着罗李两姓。根据罗姓族谱的记载,最迟在公元1000年间罗姓家族的祖先已经在富东开基。从他们讲述的方言,与赣南其他地方的客家方言比较来看,居住的时间应该比较久远,是所谓“老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罗李两姓已经成为宁都北部的大姓,仅罗氏家族就已经发展为东山、窑头、庙前三大支系,并且各自走上了家族独立发展的道路,家族制度非常完善。“文革”期间,与祠堂、庙会有关的村落组织与仪式表演也随之销声匿迹,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传统文化又被老百姓重新发明为一种与传统相连却又有别的村落文化。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围绕着族谱的一系列文字表述以及仪式表演,充分地展示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与权力,以及家族与地方文化、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1994年,受南方诸多省份民间造谱运动的影响,东山罗氏也开始酝酿续修中断了近半个世纪的族谱,这已经是第十五修了。当我来到东山罗氏的退休老师罗涛琳老先生家的时候,我看到了还保存相当完好的 《东山罗氏第十三修族谱》( 清朝光绪年间)。其中记载的修谱例则和族规族范,使我们能够看到那一个时代的国家与民间之间的互动是如何体现在民间的文字记载之中。
十三修族谱的修撰例则首先强调:“谱也者,所以明昭穆,辨尊卑,分疏戚,为一家之纲领也;盖昭穆不明,穆得以紊昭,尊卑不辩得以逾尊,疏戚不分,疏得以间戚。……昭穆正则礼义生,尊卑辩则孝悌行,疏戚分则亲亲。”谱例明确界定了家族修谱的范围,规定“嗣子继绝所以承祧,亲兄弟及本宗共姓之子得以继之。然必于其所生父下书继与某兄弟为嗣,继父下书某兄弟之第几子为嗣,互文见义,一不敢忘所自,一不混所自;其有以孙祢祖,以弟继兄及螟蛉他姓,随母嫁来者,一概不录”;对家族中的生老病死嫁娶等等,区别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的语言表达,如“丈夫死不嫁者,书守节;殁身不改者,书终节;嫁而家贫无子、与子幼无依者,书改事”。据罗涛琳介绍,而且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如“保长房,留尾房,绝中房”,也就是说万一遇上长房或者尾房的人丁不旺,后嗣乏人,就必须将中房的男丁调至长房或尾房;如果有人不愿在家谱中登录自己的名字,家族可以出面变卖其妻子儿女和土地。
族规、族约明确制定家族成员对于国家的义务,将“勤国赋”作为约束家族成员行为的第一要务;“钱粮国之正供也,朝廷之功令所系,州主之考成所关……本图粮亩散居各方,若不预为告诫,互相观望,迁延不完,将来追呼盈门,自开弊窦,贻害家庭,累无了日。后之子孙务宜传谕远近,先期早完,毋得拖扯朦胧,自罹法网。”家族成员应该严格遵守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所谓“正名分”,在他们看来,“伦纪,人之大端也。长者宜树公直之风,庶有以服其子弟者,务明孝悌之义,斯可以慰其父兄。本嗣子侄蕃衍,岂无顽愚。勿率挟势呈强者,徜不严为戒饬,徇情阿从,势必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相习成风,成何规矩,甚至内衅既作,外侮必生,族众虽繁,究无益矣。自后若有不法,严为重惩,慎勿姑贷。”为了凝聚家族成员的力量,使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和象征实体存在,对家族共同财产如祭产的管理既关涉到家族发展和对外事务处理的经济支持,也是家族精神象征存在的保证,需要“严祭祖”,严格管理家族的公共土地——族田,“祠中田租,先人之血食,派下之膏脂也。”家族田租来之不易,乃“前辈日夕拮据,不惮劳苦,置买门业,继请祔食,复制庄田,”逐渐积累。田租“每年收租除差米之外,大则可供祭祀,小则可扩众资,”在家族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族谱明确要求“值年杰士务宜秉公无私,西成东收,依时发粜,不得朦胧数目,侵渔肥己,更不许短少颗粒,上下相推”,否则“拟其不孝之罪,重罚不恕”;为了维护家族内部互助协作关系的正常运作,在事关家族纠纷的处理上,充分体现家族长老的权威,必须“敦族好”。家族纠纷具体处理应该依据一定的程序,“派下子孙……未铭(鸣?)鼓则本房为之处释,既铭(鸣?)鼓则祠中为之剖分。其间理有是非,事有曲直,杰士即当秉公而论,不得阿谀徇情。徜有不依公论,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争刚持气者,众共锄之,倍行罚赎。”在族谱中鼓励家族子孙“耕读传家”,宣称“顺逆命有定数也。勤耕力读,安分自有运来之期,诡智害人,天网自有难逃之日。”族谱强调,必须“睦亲邻”,与其他异姓家族在空间上保持独立的家族地位,对村落空间人为地设立边界,“田有井疆,山有界畔”,而这种边界概念又是以家族为认同的依据,不得混争。同时,注意村落景观的维护,“培风水”,“树木,后龙之羽毛;峦林,川流之砥柱也。前辈多方培植,实为久违之图,后人彼此胥戕,窃为柴薪之用 ,不知风水既乖,……若不严为阻绝,旦旦而伐,将来之景,况不知作何状也。”族谱还认识到“通客商”的有利性。
假如我们比较光绪版族谱与1995年版东山罗氏族谱的修谱例则和族规,可能将更有意义。1994年6月26日,来自东山罗氏大小不同房支的五十七位家族代表聚集在“罗氏大宗祠”,一致通过决定重新修撰族谱。会议产生了本届修谱机构,确立了本届修谱例则。委员会设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十名,由秘书组具体负责族谱的修撰工作,后勤组主管修谱过程中所有费用的催收和支付。这一次修谱以家族中的原村委会主任、退休干部、退休教师为主组成族谱编撰委员会,国家机关现职工作人员,包括村委会成员都没有参加族谱编撰的具体工作。族谱编撰委员会的成员意识到,传统时期的修谱例则已很难适应现时代的发展。国家人口政策的变迁带来了某些具体家庭形式的变化。在族谱修撰过程中,是继续按照传统的修谱例则,还是顺应国家形势而作出相应的修改?经过反复讨论,委员会考虑到修谱的目的是敬宗收族,团结家族的力量,族谱的修撰不以对抗国家政策的方式来处理具体问题,最后决定“废除旧社会老框框,在政府(政策)允许下定谱例。”于是,经过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新的修谱例则,规定“纯女户,已经做了招郎、顶了家产的都要上谱;同姓结婚的,应按《婚姻法》规定,五服之外的都要上谱,女的改为母姓;五服之内的,同姓结婚的,凭结婚证上谱,调丁问题采取自愿,给予上谱;不愿意造谱的人,要求其签字,但应灵活考虑;上届修谱后出生的男女都要上谱。”
从《东山罗氏十五修族谱》的族规,也可以看到民间对社会变迁的回应。下面是东山罗氏家族十五修族谱中新制订的族规(照录原文):(1)提倡爱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反对一切腐朽的恶习的思想,与一切违反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提倡讲文明讲道德,祠规要求普及理想、文化教育、法纪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2)提倡讲秩序,祠规要求做一个有益于人民对人民有贡献的人,做到勤劳致富,友爱团结,遵纪守法,不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财产,不扰乱社会秩序,对所有祠堂和庙宇和名胜古迹加以保护和维修,严禁盗窃或采取任何手段侵占或毁灭;(3)提倡尊老爱幼,祠规要求尊老爱幼,夫妻和谐,兄弟姐妹友爱团结勉励进步严格教育子女切忌娇生惯养赡养老人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坚决制止我族嗣孙不赡养老人,做不法行为;(4)培养青少年,青少年有培养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祠规要求青少年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发展,还要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祠规要求从事教育技术和其他文化事业作出贡献的青少年给以鼓励和帮助;(5)要遵纪守法,为官为民都要清廉正直,祠规要求我族嗣孙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依照法律缴纳国家税收;(6)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和包办婚姻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儿童;(7)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祠规要求凡是公有或私有财产都应受到法律保护,不受任何侵犯,祠规要求公共的或个人的财产按照法律享有继承权;(8)培育风水祠规要求对所有的祠堂庙宇及公共场所都要保持整洁美观绿化,防止环境污染对所有祠堂庙宇周围林木严禁乱砍滥伐;(9)禁赌博禁止赌博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家庭和睦,有利于青少年茁壮成长,同时还有禁止卖淫嫖娼贩毒等不法行为;(10)禁私宰,耕牛是农民不可缺少的动力对母牛种牛幼牛要加以繁殖和保护,未经兽医验明的耕牛严禁私宰 。
实际上,无论是试图解读传统时期、抑或现代民族国家时期的民间族谱,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一个非常芜杂的知识体系。尽管如此,民间族谱的知识体系——特别是经过宋明以来家族庶民化运动之后——还是地方性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扭结。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看到,究竟是谁在操纵地方社会的文字写作?进而言之,是谁在操纵地方社会的历史表述?在广大的乡间,传统社会里只有少数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人具有文字写作的权力,他们或者是应试未举的所谓读书人,或者是退休在家的赋闲官员,很多人还置有相当的田产,被乡民们称为“绅士”,有的甚至还是独霸一方的“族长”,他们或者在思想观念上与帝国的意识形态保持着一致,或者自己就曾经掌握着某一层级的国家机器。而在现代民族国家时期,却是家族中的高辈分者,国家权力的原地方代理人,国家机关的退休干部,还有并不出场的国家机关现职干部(在我调查的地方,政府禁止国家现职工作人员参与修谱,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地方社会,他们更具有影响力)。很显然,他们无一例外地与国家权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明显地优于一般的家族成员,所以,他们对家族的规范与传统更具有解释权。我们看到,传统时期的族谱修撰例则、族规族范,既体现了国家的权力意志,也体现了家族的意识形态,还体现了地方性文化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在地方“绅士”掌握的文字书写权力操纵下一种“折中”表述而已,地方“绅士”在此充当了中介的角色。而今天的族谱,虽然语言已经完成了“现代性”的转换,但是,在这种普遍化的表述中,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家族精英在这场造谱运动中,继续运用传统的表述手段,在家族/国家这一对关系中,继续扮演着传统的角色。一定时期的修谱是对家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一次梳理,在传统时期,只有男性家族成员才能在族谱登录名字,以示家族的香火绵延不绝,在当代社会的具体情况与家族血缘的理想形态相矛盾的时候,在这两者之间,家族精英显然承认了前者,使族谱的修撰得以反映家族的全貌,正是这种妥协体现了家族精英的生存智慧。我们可以发现,在族谱中,传统时期村落家族的地方性乡规民约在当代族谱中的表述并不突出,族谱中真正规范家族与村落行为准则的语言,均采取类似于国家现行法规条例的叙述方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间修谱所制定的族规,仅仅只是对国家政策和法规的简单移植,而是将民间的乡规民约和国家的政策、法规非常巧妙地揉在一起,比如,族规能够将“不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财产,不扰乱社会秩序”与“对所有祠堂和庙宇和名胜古迹加以保护和维修,严禁盗窃或采取任何手段侵占或毁灭”结合在一起来进行叙述,将表面看起来非常“现代性”的话语很自然的转换成了民间的话语,其中所表达的,无非是家族成员必须视“祠堂”、“庙宇”等为家族的公共财产加以保护,也就是说,家族试图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范围内继续诠释家族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合理性。现代民族国家时期的族规实际上也是多种知识体系相结合的产物,一是帝国时期业已形成的对儒家伦理规范的强调,二是对现代民族国家意志的民间化表述,三是地方性的乡规民约。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时期,家族精英阐释着制度化的家族体系,极力维护家族在不同生存时空的生存合理性,从这一意义理解,他们既是国家在民间的代言人,也是民间的代言人。
那么,如此一个地方历史的重建运动,普通的老百姓又是怎样一种态度?在富东村以及临近的其他几个村落,对于修谱,许多老百姓由于家庭困难,也没有人可以在族谱上光耀一笔,愧对祖先,他们也就觉得修谱没有多大意义,更遑论年轻人关注的是赚钱建房娶媳妇,对此根本没有热情,只有一帮老人在忙忙碌碌。在这一带,民间有一种说法,“铁匠望修斧,绅士望修谱”,修谱对于绅士是一个借机敛财的好机会。在邻近一个村落的李氏族众就认为,本届修谱委员会的成员有贪污的嫌疑,修谱的庄严被大大地嘲弄,以致于这一家族的祖坟在“文革”期间被人盗挖,至今也无法集资重建。民间还有一种说法,“谁先得谱,谁得福。”散谱一般按照家族房份长幼次序依次散发,由于家族内部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构怨,加上民间认为房支的强弱在于祖宗保佑的差别,通过修谱,有些房支的势力愈强,而有些房支的势力则愈弱,所以,在散谱仪式中,非长房的族众常常依仗人多势众,不按照长幼秩序领谱,聚众哄抢族谱,造成家族内部的裂痕。东山罗氏的房支力量与房支长幼次序并不一致,长房的后人远离富东,并没有占据家族政治与信仰中心的空间;二房人口最少,力量最弱;三房人口和力量都处于最强势,主要居住在家族的中心地带;尾房则居住在东山坊的边缘,人口和力量居中。为了维护家族长幼次序的尊严,防止发生抢谱行为,族谱修撰委员会决定散谱时不得抢谱,抢谱的房份罚款五百元,每房派一人做保卫工作,必须有力气,敢说话;散谱时里外共设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门外,设五道栏杆,第二道防线把守大门,第三道防线把守族谱,委员们分三班人马分别站立在三道防线上,里送外接,按长幼次序领谱。
如果说族谱是民间的历史创造,我们又将如何看待族谱的历史“真实性”?族谱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可言?从上面的调查来看,民间是否真正把族谱视为“神圣”,也许只有老百姓自己知道!更何况,在所谓神圣的背后,潜藏的可能是更多的权力与意识形态。更多的时候,族谱可能只是一种满足家族共同体想象的文字依凭,只是一堆满足民间思古怀幽情结的故纸。如此看来,族谱并不纯然是民间历史的真实写照,毋宁是一种可供分析和阅读的文本,是充满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话语。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族谱或者成为某一利益群体获取地方性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象征资本,或者充当了某一处于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共谋,或者颠覆了具有霸权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东山罗氏族谱修撰个案表明,地方性文化的创造始终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的意义,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地方性文化复杂的权力机制,即便在极端压抑的年代,民间也从未中断历史的创造。富东罗氏的族谱修撰已经远远落后于临近的其他村落。长期以来,罗氏与同居一村的李氏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从来没有处于上风,致使罗氏族众士气低沉,罗氏族众为家族的地方势力之低微而深深悲哀,同时又体会到家族整体力量对于个人与家庭的重要。正是因为周边村落家族的造谱声势,迫使罗氏的一些家族精英也开始考虑修谱,既有周边家族力量的胁迫,也有内在的凝聚家族力量的吁求。在族谱的具体表述中,家族精英极力地使地方性文化适应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而这一适应,却又以一种近乎反讽的手法将地方性文化的需求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并置起来,意欲表达的无非是地方性文化的诉求,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颠覆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由此,使我想起民间文化研究者对于民间文化的态度。自“五四”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文化代表的是“文明”的过去,“现代”的过去,是一种停滞的文化,是历史的遗留物和化石。学者孜孜以求的,是文化事相的古老与否?许多研究成果不分时空地将民间文化事相排列在一起,实际上建构的是一幅泛民族的民间文化图景。在不知不觉之中,与进化论、殖民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共谋,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所批判的忽视民间历史与文化的逻辑。这种研究取向,对所谓民间文化的研究与再现,其实淹没了民间的声音,剥夺了民间再现自己历史的能力。但是,民间并不会因为学者的盲视而停滞历史的脚步,仍然一如既往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与此相联系,1998年,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反思了西方支配的叙述将非西方民族看作是新的、没有历史的人民之观点,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在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为接受的传统与变迁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尤其明显的是,摧毁了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对立的观念(《甜蜜的悲哀》,马歇尔·萨林斯著,王铭铭、胡宗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第109-141页)。当西方人开始反思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关系的习惯想象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关于民间文化“落后”、“愚昧”、“遗留物”、“化石”之类的想象?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中国广大的地方社会纳入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地方社会的传统或者文化并不全然以现代化建设的障碍出现,我们在乡村所见到的现代化方案都是已经经过了地方化的现代化方案,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力量以诸多不同的地方性文化的图式释放出来,民间的历史创造实际上参与了现代性的本土化过程。
(本文发表在《读书》2001年第7期)
上一篇:史界瑰宝 不朽盛业
下一篇:僚人罗姓起源及罗甸国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暂无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