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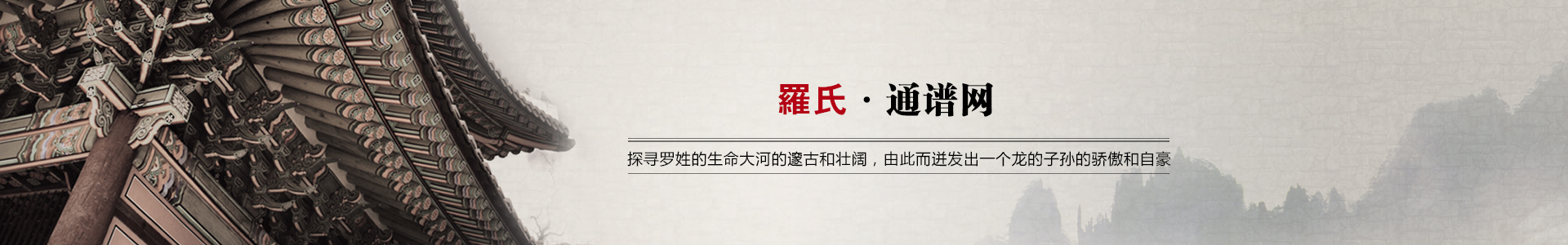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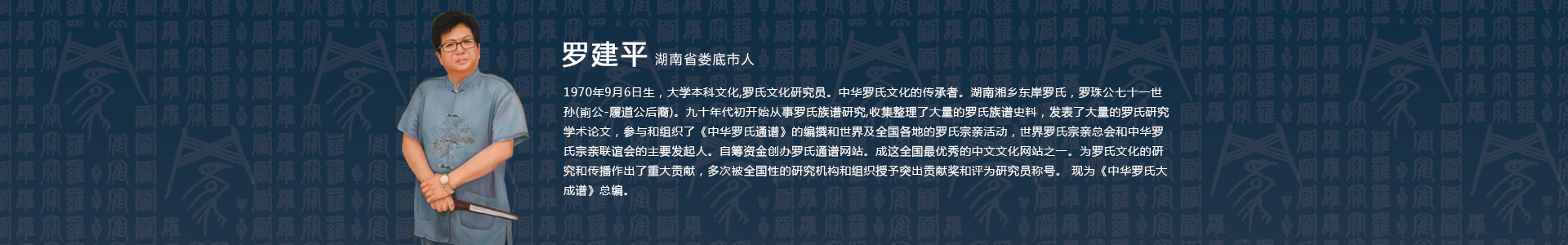
转型中的宗族与农民--罗姓村调查
罗 兴 佐 发布时间:2003-01-08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广大农村发生的诸多变化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宗族活动的重新活跃。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现象,成为各方的焦点。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一个个案透视转型中宗族与农民,并进而分析在村庄生活与治理中,宗族之间,农民之间,宗族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从一个侧面去把握宗族转型的特点及其在当代中国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村庄概况: 1、基本情况: 本文所描述的村庄——龙村1,地处赣中西部,距离乡政府约5华里。全村共有47户,224人,水田330亩,旱地30亩,山林200亩。由于村庄田亩较多,且土地肥沃,因而村庄经济一直呈稳定发展状态。除少数遭受自然灾害的年份外,农户们均略有剩余。特别是自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村庄迅速富裕起来,除几户老弱病户外,平均每户至少建有一栋新房,电视普及率近100%,其中彩电达50%以上,拥有电话近10部、摩托车近10辆,多数人家拥有数量不等的存款,使龙村成为附近的“小康村”。 2、宗族构成及其复兴: 龙村始建于宋朝,原有罗、刘、彭、朱四姓,因朱姓无后,现村庄只有罗、刘、彭三姓。自1990年代以来,各项宗族活动更是日趋活跃,罗、刘、彭三姓宗族均在不同程度得以复兴,其复兴过程又各有特点。 (1)罗姓宗族及其复兴: 罗姓为龙村人口最多的姓氏。据《罗氏族谱》记载,罗姓始祖德元系宋末从泰和匡山书院迁来。从现存房支逆推,罗姓自开基后至第六世分为三支:春风堂、柏奇堂、竹林堂。春风堂至十六世又分为三房:长房沛公、次房酉公、三房高公,柏奇堂未再分,竹林堂传至二十一世绝后,因此,罗姓现存两支四房、人口约160人,四房中各有房长,无名义上的族长,但由分属两支的两位年轻人管理宗族事务,其中一人管全面、一人管财务。罗姓宗族自开基以来,历经兴衰,其宗族活动的某些方面延续至今,尤以修谱和维修宗祠为甚。 第一、修谱; 泰和匡山书院罗氏自洞晦开基以来曾十修其谱,龙村罗氏自德元开基后一直未能修谱,直至清乾隆后才五修其谱,分别为乾隆五十二年、道光十年、光绪四年、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九五年。在1995年修新谱以前存有民国十三年所修旧谱。1995年所修新谱乃与泰和匡山书院同修。其过程大致为:1995年5月总谱局成立于书院坑、由十多个村庄组成。龙村罗氏族内辈份高的年长者罗为长到谱局开会,统一修谱思想,商定有关修谱事项,回来后召集罗氏四房房长开会,传达总谱局有关决定:(1)规定由别姓买来者不能上谱,同姓不同宗不能上谱;(2)修谱费用按50元/人募集,分期分批交至总谱局。龙村设立分局,由罗建彬具体负责。8月份,罗建彬带老谱、草谱至书院坑总谱局,由掌稿人审核、排印,每印一张都即时校对,有错即时更正,历经三个月才将新谱的底稿弄好。其间,龙村罗氏族内多人多次到总谱局参与有关事项或做客,至11月底新谱正式开印。开印期间,所有工作人员按时作息,各工作人员亦抱着对先祖负责,继承祖宗遗业思想,工作兢兢业业。龙村建彬在总谱局印谱13天,直到全部印完后,装订成册,装入谱箱才回家。 新谱修好后,最为热烈、隆重的是接谱。龙村与书院坑相距约6华里,1995年12月18日,龙村罗氏请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在村庄吃过早饭后出发到书院坑接谱,由于担心别人抢谱,包括吹鼓手一起十余人,开着车,放着鞭炮向书院坑进发。至书院坑后,按事先用石灰在公路上划定好的位置在祠堂外等候。祠堂里庄严、隆重,门口两边站着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只有佩带红布制作的工作证的工作人员才能随便进出。接谱按从书院坑迁徙出去的辈份的大小排列顺序,当接谱的村庄进入祠堂后,放鞭炮、敬祖宗、击大鼓,然后由两人将谱箱抬出祠堂,敲锣打鼓接至车上。龙村共领两箱谱,一路上吹鼓手吹打不止,每遇村庄便放鞭炮予以明示,族谱接至村庄后,先送至罗氏宗祠敬祖先、鸣爆、击大鼓,然后敲锣打鼓送至保管谱的人家中。当日,罗氏宗族在宗祠里大摆酒席,所有罗姓男丁都参加,其场面之隆重直至今日人们谈起来仍绘声绘色、津津乐道。 第二、维修宗祠: 宗祠在罗氏宗族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除“文革”期间外,宗祠一直是罗姓宗族活动的中心,女儿出嫁要进宗祠,以证明她的纯洁;娶媳妇要进宗祠,表明其取得了族人的认同;在村庄内过世的老人也要进宗祠,以免于成为孤魂野鬼。 据《罗氏族谱》记载,龙村罗氏先后共建了十座祠堂,并且集中在清康熙、乾隆年间,目前仅剩四座。罗氏宗祠始建于清乾隆甲辰年,1969年山洪暴发,祠堂倒塌前栋左边砖墙,次年即修好了。当时祠堂已收归生产队所有,用作仓库,故经费、劳力均由生产队调配,因此并不限于罗姓人参与修祠,但修祠劳力的吃饭问题由罗姓人解决,此后对该祠堂亦经常检修,目前,该祠堂终日敞开着大门,但由于宣布了有关管理要求,因而堂内十分整洁,并无乱堆乱放现象。另一祠堂春风堂(支祠)现为村小学所在地,1971年亦大修过一次,此后也经常检修。还有两个房祠,一个始建于乾隆五十二年,至1969年涨大水时几乎完全倒塌,1971年同样以生产队名义重建,辟作仓库;另一个已濒临倒塌,房内正在酝酿维修。 (2)刘氏宗族及其复兴; 刘氏系富田锦溪刘氏的后裔。相传锦溪刘斗圩官居柱国,阻拆富川石陂放运皇木而触犯皇帝,免官归里,株连九族,被迫流放逃亡,龙村刘氏即是此时从锦溪逃来的一支。据《刘氏族谱》记载,自清未徙居已历八世、现有三世,仅一房(四代以上即为同一祖先,加上人少,刘姓人自认为是一大家)8户35人。刘氏存有民国二十九年所修族谱。1995年与邻乡的草坪村同修了新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氏宗族于1999年新建了刘氏宗祠。据说刘氏徙居龙尾村以来一直单传,故村庄有“刘家只留一家”的戏语。因此之故,刘姓一直未建祠堂。近两代以来,刘姓人口日渐增多,随之而来的婚丧嫁娶之事也日益频繁,尤其是现存第一代的刘氏四兄弟中已有三人年过花甲,已面临着过世后何处守灵的问题,过去因为此问题曾受到罗、彭两姓的嘲笑,加上经济上日渐宽裕,终于促成刘氏宗祠的兴建。1999年刘姓人按户均3000元,每个男丁1000元募集建祠经费四万多元,前后历经三个月建成刘氏宗祠。宗祠落成后,按村庄惯例,每户请一人前来庆贺,同时请来了罗、彭两姓的老成斯文,罗、彭两姓各买了一万响的鞭炮以表祝贺。 (3)彭氏宗族及其复兴; 据传彭氏为龙村最早的居民,系宋末从本乡的潢汾迁入,因人口增加,一支迁居到本乡的枫树塘,留在龙尾村的彭氏却呈衰败之势。现有4代,分两房,5户25人,有旧谱,92年曾与枫树塘(该村有彭姓十多户人家)同修族谱,因不愿再出400元购一箱谱,所以无新修族谱。彭姓有总祠永思堂,但并不为龙村彭氏所独占,而是与枫树塘共有,该祠堂在1970年与罗氏宗祠崇义堂一起以生产队的名义维修过一次。此外,彭氏还有一祠堂,名为嘉会堂,集体化时期,该祠堂一直为生产队仓库,因而也一直以生产队的名义维修着。自生产责任制后,祠堂归还彭姓人管理,彭姓人亦不时对祠堂进行检修。由于修谱和修祠后,彭姓人并未添丁2,所以谈起此事,彭姓人似乎透露出深深的失落与无奈。 综上所述,龙村是一个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小村庄。自1990年代以来,村庄内的三个宗族均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复兴。从其复兴的过程看,罗姓作为最大的宗族,其宗族活动相对比较活跃;刘姓因现存的第二代比较发达,在追求宗族器物层面的同时,也在日益寻求着与村庄人尤其是罗姓人在村庄事务上的平等权;彭姓人在近几十年中已呈衰落之势,因而在村庄事务中表现为更多的妥协与认同。但从目前所呈现的结果看,宗族的利益仍没有打破村庄原有的人际关系准则,传统的规则仍在规范着人们,并指引着人们的合作行为。 二、村庄生活中的宗族与农民: 1、新型村落权威的突显; 一般而言,在村落存在着三种权威:一是宗族权威,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宗族生活中,人们屈从于宗族文化的权威;二是村落权威,它以地域范围为特征,在村庄的人际交往中,人们服从村落文化权威;三是行政权威,它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在国家与村落的关系上,人们以维护行政权威为理性选择。这三种权威可能同时存在,也可能表现为一个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 建国前,宗族组织较为完善,宗族功能亦较为突出,因而在村落中,人们认同宗族权威,寻求与宗族的合作与保护,宗族成为人们对外交往的象征资源。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体制对宗族文化的冲击,宗族权威被来自国家的行政权威所取代,宗族活动被停止,宗祠、家谱等被作为“四旧”而扫荡,农民转化成为强大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细胞,集体化的生产成为人们的生活之源,基层政权组织成为人们唯一可以而且必须依赖的权威。但这种情况在推行生产责任制后却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的生产生活回复到家庭单元化阶段,宗族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复兴,消解着行政力量的权威;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基层政权组织、自治组织功能的单一、利益取向与农民的要求存在一定的矛盾,造成乡村关系紧张,因而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威亦流失严重。而与此同时,尽管宗族已经重建,但它必须是在现存国家体系的框架之内,因而传统的宗族文化权威即使有所抬头,它仍然被抑制着。因此,作为最终结果的现实是,宗族的传统权威未能重建(至少在龙村是如此),而正式组织的权威亦未能真正主导着村落。然而,村庄毕竟需要权威,尤其象龙村这种处于善治的村庄,它就是新型的村落权威。 新型村落权威体现着权威的综合。它既有基于地域的公共权威,又有基于血缘的宗族观念,还有生存于村落的传统习俗(并不是宗族的内部习俗),这里的习俗亦不仅仅是一种表象(王沪宁1991),而是一种权威的综合,是真正支配人们的主导权威。在村落中,权威往往并不单纯体现在具体人身上,尽管龙村确实有一群村落精英,但问题主要不在他们个人,而在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村落文化中那种宽容、公益、勤劳、大方的内涵,与其说他们代表着新型村落权威,不如说权威体现了那些人们公认并欣赏的村落文化。龙村的罗为长、罗建树即具代表性。罗为长系罗氏宗族辈份最高的年长者,1960年代曾任大队长,回村后担任生产队长十余年,直到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才卸任。由于其拥有的宗族与政治资本,加上他处处维护村庄利益,因而在村庄中拥有较高的地位,人们都非常尊重他。然而,近些年来,人们开始嫌弃他了,一则因为他爱贪小便宜,常把别人家鱼塘中半死不活的鱼捞回家;二则爱干损害村庄公益的事,经常到村里的竹林里掰春笋吃;三是因为他有些钱,应急时村民不得不找他借,但他却向村民要高息;四则因为他闲着无事,喜欢在村里串门,尤其喜欢凑热闹,专往有事的人家钻,因而免不了被人们招呼吃饭、喝酒,可他常在饭桌上大发议论,唾沫四溅,十吃八醉。正因为如此,尽管人们表面上仍然对他表示尊重,实际上嫌得很,即使在罗姓宗族中,人们亦常不卖他的账。与此不同的则是罗建树的崛起。罗建树的家庭出身并不好,其父被划为村庄上仅有的两户富农之一,在“文革”中屡次被批斗。自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担任村小组长,在其任职十余年间,组织村庄开展了一系列公益事业,在能力上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再加上他为人谦和,办事公正,富于公益心,因而博得了村庄的普遍尊重。可见,新型村落权威的生长,反映着它对村落文化的体认,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权威的综合,它深深地溶入到村落文化之中,因而能够成为主导村落的真正权威。 2、宗族仪式的形式化色彩; 如前所述,自1990年代初以来,龙村的罗、刘、彭三姓宗族均在不同程度上重建了。实际上,就宗族生活的某些仪式活动来说,早在1970年代中期后便逐渐得以恢复,并延续至今。但考察这些活动,我们不难发现,在追求其本体意义中往往流于形式,是形式的而非功能的。龙村罗姓的修祖坟祭祖和大年初一拜祖则生动地体现了仪式的形式化。 罗姓祖坟保存之完整实属罕见。罗姓自宋末德元开基以来已有七、八百年之久,然而由于后人不断维修,至今始祖、二世祖、十六世祖的坟均非常完好。始祖墓在1974年被重修,二世祖墓在1999年再度重修,所需费用均按男丁摊派。1999年修二世祖坟时按每个男丁10元募集,每户出一名男姓劳力,花费一天时间,修完后举行祭祖仪式,所有参加修墓的男丁会餐。近些年来,罗姓冬至扫墓之风日盛,每年冬至前后,罗氏宗族的两位负责人(召集人)按每个男丁10元收集款项,然后置办好扫墓、祭祖所需物品,如腊烛、草纸、香火以及肉鱼等食品。扫墓之日,一般由负责人通知每一大家3的说话人,由他去转告其他各户,每户一名男丁参加,很少出现不来的情况,由一世祖、二世祖开始。尽管自六世祖和十六世祖后已分为不同房系,但只要是已经辩认出的祖坟都会顺路拜祭。一般是先清除杂草、荆棘、整理好墓前的空地,然后摆上各种各样的杂品,点上蜡烛和香,烧纸、放鞭炮,接着按辈份大小排列成行进行跪拜(实际上除第一排外,其他并不严格要求),每次仪式结束后,参加扫墓的男丁照例会餐。 罗姓宗族还有一项重要的宗族活动是大年初一到罗氏宗祠去集体拜祖。该项活动自1980年代初恢复以来一直未曾间断。每年的大年初一吃过早饭后,罗姓宗族的两位负责人便去祠堂放鞭炮开门,并摆好两张桌子,备好红纸、墨汁和毛笔,并准备好贴对联的米糊。族内男丁在村庄中拜完年后便陆续集中到祠堂里来,读书人便被要求写对联,这对读书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一则对联的内容有一定的讲究,凡贴到上厅的对联必须钳入祠堂名,而贴到祠堂大门口两根石柱上的对联则不仅要钳入祠堂名,而且还要钳入村名,那些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对联只能贴到堂内另外的柱子上;二则对所写对联有一定的书法要求,因为对联必须当堂写,只有族人感觉写得不错的才能被贴到显要的位置上。正因为如此,读书人中多有练习毛笔字的传统,尤其是有些遭到族人排斥的两户人家的子弟更是如此。一户与龙村罗姓同姓不同宗,一户是五代以前从外地买来的,因为上述原因使该两户在宗族活动中常遭冷落,而这两户为了显示其子弟的才华,各有一位苦练书法,每年大年初一时便到祠堂里去写对联。尽管被贴到显要位置的次数很少,但通过比较他们确能获得一种内心嘲笑他人的快感。对联贴好后,常常由族内辈份最高者召集族人在上厅向祖宗拜年,人们一般自觉按辈份排成数队,然后放鞭炮,作揖打拱,跪拜祖先。拜完后,众人便坐在祠堂内喝开水,吃点心,听老年人讲宗族、村庄过去的事。 扫墓与拜祖作为罗姓两次大的宗族活动,自恢复以来一直坚持着,成为惯例,但除了其表面的形式外,似乎对强化人们的宗族认同,沟通人们的血缘感情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其一,对活动的参与并无明确的规定,是否参与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态度,既没有相关的激励,也无相应的制裁,因而人们完全是自由的态度;其二,活动的参与者多为户主,并未扩展至全体族人,其对活动带来的吃喝的功利性要求远远超过对宗族文化本身的体认,因为即使某一户主没有来参与扫墓,吃饭时人们总会去叫他,毕竟他家也是出了钱的;其三,在活动过程中还有可能激化宗族内部的各种矛盾,如前述写对联,常引起人们春节后的议论。可见,宗族仪式多有流于形式之嫌,即使我们撇开它可能导致对宗族的负面效应不谈,也不可高估它对于强化宗族认同,增进血缘情感的作用。 3、村落纠纷的逻辑顺序 龙村是一个小村落,龙村的宗族亦是小宗族,但同样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考察各种纠纷发生的频率,我们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呈现着由家户之间的矛盾到族内房与房之间的矛盾再到宗族与宗族之间的矛盾的递减趋势,由此亦可判断出村落大量的、主要的矛盾是家户之间的矛盾。 家户之间的矛盾是经常的,因为村庄作为一个固定的生产生活区域,尽管自生产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户的利益已经单元化了,你种你的田,我吃我的饭,主体界限非常清晰。然而利益的实现却仍然是连在一起的,你家的牛吃了我家的禾,刚晒完田你就要过水,甚至小孩打架也能引起大人的吵口,矛盾真是时时有,不仅有为实体利益的,也有为面子的。在同一宗族内部的房与房之间也有矛盾,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罗姓宗族上。罗姓目前存有两支四房,各房之间存有不同程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既有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有因现实中的纷争产生的。从历史上看,罗氏向有冬祭、春祭两次集体祭祀活动,其经费由族田之中的冬祭田、春祭田的耕作者提供(罗氏族田分四类,除冬祭田、春祭田外,还有谱会田、灯会田),祭祀时,所有族人都必须参加,但祭祀完后参加家族会餐则必须是拥有会名的才能有资格。而会名是在某一时期按房平均分配的,罗姓的会名是在十五世祖时确定的,当时十五世祖有三个儿子,加上六世祖另一支单传,共四房,按每房五个名分予以确定。然而,由于各房人口繁衍的差异,往往几代以后,形式上分配的平等便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男丁发达的房所需会名不足,而人口不发达的房则会名有余,但由于沿袭历史的因素,这种事实上的不平衡却无法打破,以致于大房不得不向小房购买会名,这造成了大房人的不满,由此积下矛盾。尽管自解放以来祭祀被禁止,家族会餐被取消,会名亦失去了价值,但积下的矛盾却并未释解,至少房与房之间的隔阂是非常明显的。在现实中,因为一些实际的利益问题也会发生矛盾,不过这种矛盾往往是由家户之间的矛盾扩展的,所以并不尖锐,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相互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 在龙村,罗、刘、彭三姓之间未发生带宗族性的矛盾,这里的问题是异姓农户之间的矛盾一般不会上升至宗族矛盾,尽管其背后有不同的宗族基础。2001年4月的一天,住在村庄前面的一刘姓青年用语言侮辱一罗姓妇女,该妇女的三个儿子狠狠地凑了刘姓青年一顿,尽管该刘姓青年亦有四兄弟,但未敢前来帮忙,事后,除刘姓青年的父亲对着天骂了几句外,事情基本上被平息。在村庄内,异姓之间也经常因为一些实际的利益发生口角,有时甚至也动手推拉几下,但基本上限于农户之间,不会扩展至宗族性矛盾。 三、村庄治理中的宗族与农民: 1、宗族边界的模糊与清晰; 龙村是一个杂姓村,虽罗姓占绝大多数,但由于村庄规模较小,各姓历来相安无事,以罗姓人的说法是,人家是小姓,何必欺负人家呢。并且,在历史上,村庄曾经共同举办一些民间仪式。据说村庄原有每年都要举行送神活动的传统,该活动从大年三十开始,人们将一幅画神挂到罗氏宗祠崇义堂的上厅,同时摆出四尊菩萨,设神台、摆桌凳,每户人家都要到祠堂里去敬神,谓之起神,一直到二月初一。村庄上,每天一户轮流到祠堂里去守神,并供养全村的老成斯文,谓之当神。轮流不限于罗姓,当时刘姓只一户亦参与轮流、彭姓因较贫未能参与,但也可祠堂里敬神。二月初一那天,村庄人抬着用纸糊就的花轿、龙船、菩萨至河边,一路上,老成斯文念着祭文,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然后烧掉花轿、龙船。是日,龙村热闹非凡,村庄上各家各户的亲朋好友均来看热闹,是谓走下元霄,每户人家均有几桌客,为此,一般人家均备有两套以上的桌凳和碗筷,否则无处借用,因此,这一天成为村庄上的共同节日(在附近五华里的范围内仅龙村有此活动)。时至今日,村庄过下元霄的气氛仍不减当年。 村庄传统的互助互庆亦促进着村庄人的团结与友爱。龙村自清末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村落,因此,在平时的互助中就不能仅限于本姓,尤其刘、彭两姓。近年来,村庄上凡建房、喜事、丧事之类需大量帮手时,人们都得请人,而凡被请者均会乐意为之,且只供伙食,不计报酬。村庄上还有共庆的传统。凡村庄上每户人家的红白喜事的酒席,除本房大小人等一律参加外,还会按每户请一人,帮忙的再增请一人来参加酒席,这一传统有助于增进村庄人的宽容与共处。此外,龙村罗姓与刘姓、彭姓之间均存在姻亲关系,因而,在扩大的姻亲称呼上,人们都能以舅舅、老表称呼对方。因此,在实际生活中,龙村的人际关系网中还增加了亲缘因素,这也有助于降低人们的宗族隔膜心理。 可见,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在龙村宗族的边界是模糊的,这种模糊使得地缘利益超然其上,在村庄治理中,农民们溶入到村落的地域概念中,从而有助于村民认同新型村落权威及其建立于其上的公共权力机构,保持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然而,在村庄治理中,宗族的边界有时又是清晰的,它突出表现在:第一,在村庄治理事项的酝酿中,村庄公共权力机构一般会主动地听取各宗族的意见;第二,在一些难度较大的事项上(如集资),除了召开全村户主会议予以布置外,一般先与各宗族(包括各房派)的说话人事先商量,如遇阻力,也依他们去解决;第三,在村庄管理中,充分考虑到各宗族(包括各房派)存在的事实,村庄桥梁维修委员会(桥会)的组成便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桥梁修好后,人们在庆功酒席上议论要成立一个桥会来负责桥梁的管理与维修,大家你一言我一句便把这个名单确定了,不是人们早已议定好,实是人们对村庄宗族、房派的清醒认识,因为从桥会组成人员看,他们几乎均匀地分配在各房派中。龙村三个宗族共七房,每房一人,加上两个村小组长和一个负责人,正好十人,并且若要调换,一般也局限在本房内。在这里又表现出了宗族、房派边界的清晰,这种清晰实际上又提高了村庄管理的有效性。因为它包含着对村庄宗族、房派存在现实的认可,体现了公平、公正地对待这一事实的观念,因而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2、正式组织村庄功能的持续; 应该说,自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由生产队演化而来的村民小组的功能大大衰弱了。在基层组织体系中,村小组长除了去村委会开会分摊税费任务并填在农民负担卡上分发给农户以及在村委会集中收粮收款时参与本村庄的工作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事要做。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村庄,村小组长似乎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了。然而,在龙村,情况却有些不同。以村民小组为组织依托,以村小组长为核心,村庄人兴修了一系列村庄公益事业,表现出了村庄高度的自主治理能力。 在龙村的一系列治理事件中,突出的是修桥与修路。 (1)修桥; 龙村背靠富水河,历来交通不便。原先龙尾村人依靠一座小木桥与离村庄约1.5华里外的一条沙石公路(吉富公路)对外进行交通联系。在1970年白云山水库修建以前,每遇大雨,富水河都要涨大水,因此,据说那座唯一便捷通向村外的小木桥在解放前被洪水冲跨后一直没有再修了。从那时起,村庄的对外交通联系要么拐一个大弯经王田曾家、朱家木桥,要么直接涉水淌过富水河。集体化时期,由于在王田段搞田园化,横纵修了两条机耕道,可供拖拉机行驶,因此,那时亦可利用这两条机耕道东与富田、南与苑前、西与云楼保持车辆交通联系,大型拖拉机可直接开进村庄来运粮,小车也可直接将在外工作的干部送到老家的门口。然而,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由于荒于管理与维护,昔日宽阔的机耕道被道旁两边水田的农户不断掘取,变成了仅能通板车的乡间小道。至此,龙村人只能兜一个大圈,或步行或骑自行车去赶集,而卖粮则必须一包一包先驮过富水河后才能装运上车,这成为龙村人的一块心病。一则河水涨落不定,每遇涨水便无法涉水过河,二则春去冬来,每到寒冬人们便不得不忍受刺骨的河水,尤其是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实施,龙村的粮食产量剧增,每年村庄均有数十万斤的余粮要售给粮站,因而每遇秋收后卖粮,有时人们甚至不得不只穿短裤,淌着冰冷的河水将谷子背到对岸,因而修桥一直是所有龙村人的一个心愿,并且这种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终于在1993年由龙尾村两个小组长牵头,成立了修桥委员会,着手进行建桥工作。首先是筹集资金。资金的筹集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村庄原有的卖松枝的资金约一千元,二是村庄在外工作人员的捐款约四千元,三是村庄内集资按人均10元,户均15元共筹集约3千元,总计八千多元,其次是购买材料,由两个小组长出面,通过乡政府和白云山林管站购得数立方米木料;三是将修桥的木工活承包给村庄上的木工。上述工作完成后,由两个小组长安排劳力,按每户一天一人,劳动力多者则愿多来,所有参与修桥的劳力除统一安排伙食外,均不计报酬。历经三天,终于架起了一座长约60m,宽约60cm的木桥。 (2)修路; 近十年来,龙村共维修了两条乡间道路。一条为村庄经木桥至吉富公路,这是村庄通往村外的交通要道。该条路分为两段,一段在村庄内,即从村庄至木桥,一段在村庄外,即木桥至吉富公路,可通行汽车,属多个村庄共用。村庄外这段路在集体化时期已经修建,但由于路基为泥土,车辆通行后易形成两条深深的车轮道,并且一旦下雨,车辆便很容易陷进去。按理该段路属多个村庄共用,理应由共用村庄来共同兴修与维护,然而十余年来,由于各村庄分属两个村委会,人们无法组织起来,因而该段路也一直为龙村人所维护。每遇村庄卖粮时,龙尾村两个小组用村庄积累的资金购买块石,按户安排劳动力将路面铺平,因此该段路每年至少大规模维修两次,除劳力不计报酬外,还需花费数百元;该条路在村庄内的这一段,原仅为一条小路,自板车桥修建后便将路面拓宽成可通行板车的村道。由于路面拓宽占用了村民的水田,两个小组按均分的原则进行补偿,村民没有什么异议。 村庄所修的另一条路为村庄至尼姑岭的田间道路,该条路主要为村民集体牧牛和田间耕作提供便利。集体化时期,它是当时所修的两条机耕道之一,至少有3m宽,可通行拖拉机。自生产责任制以来,该路遭到严重破坏,不仅路两旁的排水沟被外村农户变成了自己责任田的一部分,使路面仅存1m多宽,而且随意挖断路面放水,以致于在许多缺口处连小牛都会摔死。1994年村庄两位小组长做了大量外村农户的思想工作,他们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服路两旁的农户,以原路面为基础,在路两旁修建了两条排水沟,并且每遇排水缺口都埋下水泥管道,从而保证了路面的平整、畅通。此后,龙村每年至少要大面积维修两次,主要是用板车运来沙子填平路面,并且清淤排沟,保水畅通。参加修路的劳力同样由龙村两个小组长安排,并且不计报酬。 从上述事件,我们可作如下分析:第一,村民小组对于村庄仍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组织,它能够整合村民的利益诉求,村民亦认同这一正式组织的组织功能,服从它的调配;第二,村庄精英必须借助于正式的组织资源。罗建树确实有些能力,个人素质亦较好,但他主要是通过担任村小组长得以体现的,正是因为他有这一正式组织身份,才赋予他一系列行为的合法性。第三,正式组织亦为上下沟通提供了合法身份。在村庄各项公益事业的兴修中,村庄人总是希冀着能从村庄外获取额外资源与便利,而在目前的政治生活中,只有依托村级正式组织才能进行上下沟通。在修桥中,正是罗建树数度往返于乡政府和白云山水库管理局才从乡政府取得了购买木料的便利,并为村庄带回了1500元的捐助。可见,在村庄治理中,农民身份主要是村民而不是族民,组织者主要是正式组织而不是宗族,尽管后者并不能忽视,但它主要是潜在的,处于隐形状态,突显在实际动作过程中的仍然是正式组织及其资源。 3、村庄舆论的评价与整合功能; 村庄治理诸事何以达成,治理过程中各方力量何以互动?因而存在着一个评价与整合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村庄舆论及其扩散效应。 村庄舆论往往起源于非正式场合。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彼此间面对面的交往非常频繁,村庄上的许多事情往往都起源于村民日常交往中的非正式论坛。夏天的晚上人们通常喜欢坐到村庄的空旷地来乘凉,冬天人们又总爱一起围坐在火炉边烤火,村庄上人家的婚丧嫁娶人们又往往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甚至在田间地头干活时,相邻田的农户亦可大声交谈。一句话,村庄非正式论坛的场合、机会实在太多。人们交流着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村内村外,人与事,人们无所不谈,村庄治理诸事恰恰就发端于这样的闲谈之中。如重修板车桥之事,因为村庄上有人了解到邻乡有一村庄修了一能过板车的木桥,然后将此消息予以传播,这才开拓了村民们的思维。在人们的观念中,过人修木桥,过车则必须修水泥桥,而对修水泥桥村庄人是不敢想的,根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木桥修好后,村民们没有再想修桥的事,但当可以修板车桥这一新名词在村庄上传开后,人们议论纷纷,并很快达成了共识。 当然,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操作起来就没有困难,毕竟做比说更难。因此,当村民们对某事有了相当的共识后,便由村小组长出面组织户主会议,往往在村小组长的家里召开,这可看作村庄的正式论坛,一般是由小组长提出一些想法后,村民们便进行讨论。再以修桥为例,诸如如何筹集资金、哪些人负责,具体怎样操办等,均在会上讨论确定。这种场合,发言者多为村庄中能够管些事的人,包括家庭的、家族的,一般人则要么附合、要么沉默,因而讨论进行得相对充分,一旦形成决议,便成为村民们必须予以遵守的准则。 正式论坛达成共识后,村庄舆论又转入非正式场合。这时,人们的谈论便有了选择性,一是人们对决议当中不符合自己想法的说三道四,二是对那些未能及时履行决议要求的村民提出私下批评,因此,这时的议论又变得嘈杂了,但因为有相当的共识,所以主流倾向是对那些持异议者进行批评,尤其妇女们在私下的交流,这种批评往往极为刻薄。这样一来,基于共识的村庄舆论便构成村庄生活中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是没有村民能够抗拒的。 在村庄舆论这样一个简单的流程中,包含着各种主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首先,村小组与村民的互动,这是清晰的,因为在多姓村,唯有村小组才更备组织起村庄人的权威基础;其次,家户之间的互动,这是直接的,因为它涉及到对现实利益的分配,如集资是按户还是按人则区别很大,人多的主张按户,人少的倾向按人,免不了要谈判、妥协;再次,宗族之间的互动,这是潜在的。龙村是小村落、小宗族,尽管从未发生过宗族性矛盾,但三姓七房却是明显的,因此,如何保持他们之间的均衡,虽不用明说,但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因而,凡涉及村庄事务都得尽量考虑这种宗族格局。 可见,在村庄治理中,人们借助于村庄舆论,既整合了人们的利益诉求,又实现了各方的互动,从而把村庄治理纳入到良性的轨道中。 四、讨论:关于宗族重建与转型的话题 自1980年代以来,宗族在不同地区得以不同程度的重建,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并且它已经不是旧宗族形态的简单重复和翻版,而应被看成是传统宗族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产物(钱杭,1995)。然而,对于宗族转型过程中的特点,仍然需要人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首先,关于重建对宗族本身的价值认识。一般认为,修谱、维修宗祠等宗族重建活动对于整合宗族认同,增强人们的血缘情感,提高宗族的凝聚力具有积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用的程度尚需人们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从龙村罗姓宗族来看,其重建的作用似乎并不明显。相对来说,罗姓比刘、彭两姓宗族活动、仪式更具规模性和程序化,但它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正向后果。如前所述,罗姓的家族活动多数限于男姓户主,当然它并不排斥其他人参与,但在仪式之后的会餐则只限于参与的男姓户主才有资格(当然也可被其他家人替代),因此家族活动实乃家族内部的一次户主聚会,并未覆盖于全族人,它似乎表明着仪式仅是族人对先祖的一项义务,寄托着后人希望不断得到先祖神灵护佑的期望心理,而从实际的结果来看,它并未降低宗族内部各户之间的纠纷,吵口,打架亦是族内的常事,尤其是人们的房派意识变得更加突出了,它似乎又在消解着宗族仪式的整合功能。当然,罗姓是小宗族,情况要好得多,龙村附近的一个大姓宗族,在宗族重建之后,各房之间的争斗变得十分尖锐,以致连村委会干部也选不出来,村庄治理陷于瘫痪4。也许只有当宗族受到外族欺负时才能显示其内聚力,但这又不一定非要以宗族重建为前提。罗姓曾在1976、1989、1993年三次与邻村因祖坟山地之争几成械斗,罗姓宗族表现出了很强的团结性,但那时罗姓宗族并未重建5。因此,似乎并不能过高估计重建对宗族整合的价值,关键还在于宗族本身的特质。 其次,关于宗族重建的基础问题。宗族重建除了有其心理需求以及适宜的社会条件外(钱杭,1995)还有其本身的基础问题。人们在谈论宗族重建时常有此论,以为重建就是在完全被破坏甚至完全不存在的背景下展开的,其实不然。诚然,建国后的历次运动确实使原有的宗族遭受了打击,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如没收族田、推倒祠堂、焚烧族谱、批斗族内头人等。显然,这些多属表层的、外在的,蕴涵于人们内心的那份血缘情感、宗族认同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着。而龙村的罗氏似乎就更幸运,不仅器物层面的东西损失较少(仅没收了族田、焚烧了几尊菩萨),并且人们的宗族情感也没有被抑制,典型的表现在村庄对外村地主来龙村进行改造这一事件上。人民公社时期,为了便于对地主、富农管理,避免本村对其妥协,而将地主、富农调村改造。1971年2月,邻村(与龙村相隔五华里)一罗姓地主被安排到龙村来接受改造,然而该地主在村庄“改造”了近五年,却不曾受到不公正待遇,以致于到最后竟不愿回原籍。问及村庄人当时何以这样做,罗姓人均说有宗族观念。可见,即使在那个时期,宗族依然存在着,依然在村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它所抑制的仅仅是宗族仪式,而不是本体意义上的宗族。因此,自1980年代以后的宗族重建并不一定是在宗族趋向衰亡这一基础上(赵力涛,1999),在一定意义上,毋宁说是现时代的人们选择性地恢复着过去曾被抑制的宗族仪式,是一些传统仪式的重新拾取,尽管它已经被人们赋予了一些新的内涵。 再次,关于宗族转型中的农民问题。自1980年代初以来,各地的宗族重建象一阵风似的,一个接着一个,人们争先恐后,并且攀比着。其实,考察各地的宗族重建活动,是否可作如下归纳:第一、农民是能够理性对待宗族重建的。根据肖唐镖先生的研究,在宗族活动中,多数农民持“随大流”或“无所谓”的态度,积极分子和持消极态度的农民并不多(肖唐镖,2000),这反映出在宗族重建活动中,农民依然是理性的。龙村罗氏四房对于维修房祠的态度可见一斑。罗氏四房房祠作叙堂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间虽曾多次修复,毕竟年代久远,梁木腐朽,至今已倒塌了三分之一。近年来房中有人倡议,欲大修,但预算经费需一万多元,每户均摊上千元,所以一直得不到房内大多数人的响应,而任凭它倒塌。可见,即使对于宗族象征的祠堂,人们也能理性待之。第二、在宗族重建活动中,农民表现出了对宗族一定程度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既体现了农民对自身历史感和归属感的体认,也反映出了宗族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即宗族的重建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第三、转型的宗族组织作为一种弱式结构(钱杭,1995),已经大大地丧失了对农民的约束力,毕竟现代法制观念在不断得到普及,毕竟现代组织体系在日益完善。 总之,中国社会从20世纪开始进入转型时期,这个总过程是村落宗族文化嬗变的不可缺少的前提(王沪宁,1991),考察宗族的转型不可脱离这样的前提,但似乎还不够。宗族作为一种历史久远的世系群组织,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赋予了不同的宗族以不同的内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性,因而宗族的重建也好、宗族的转型也好,都不可一概而论,而应当把问题放到特定宗族的历史与现实中加以分析。唯有如此,方可客观、公正地看待宗族重建与转型问题,避免以偏概全。 主要参考文献: 1、钱 杭:《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2、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肖唐镖:《宗族》载熊景明主编《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4、赵力涛:《家族与村庄政治1950—1970》,《二十一世纪》1999.10。
上一篇:史界瑰宝 不朽盛业
下一篇: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 常建华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暂无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