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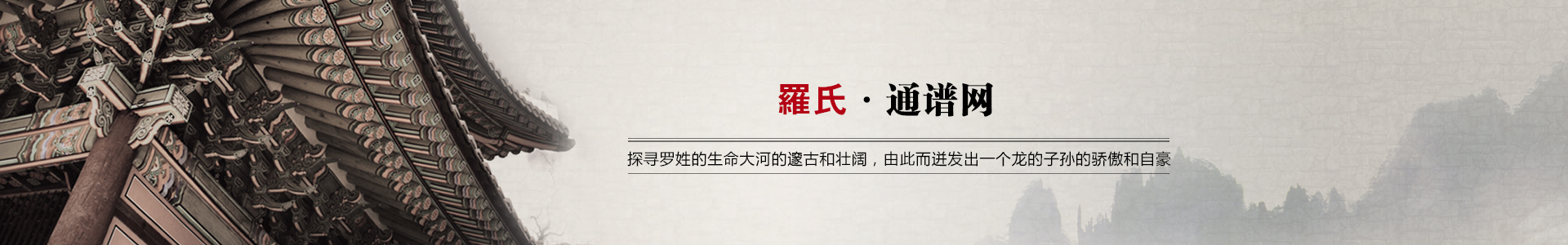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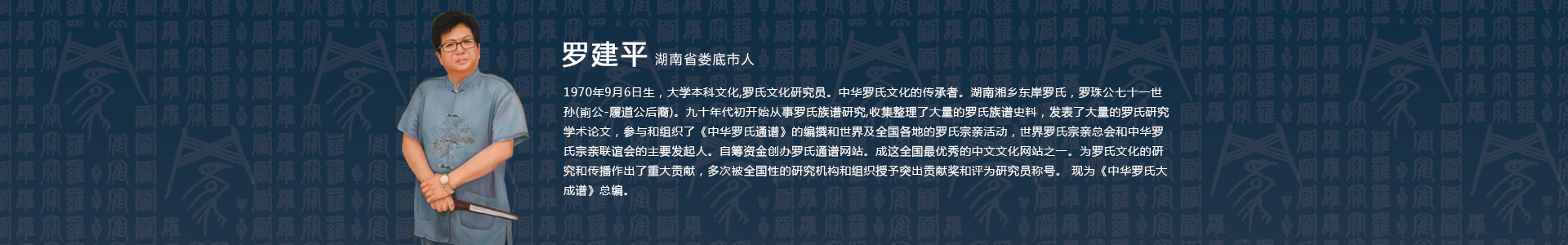
罗泽南辨学思想简论
张晨怡 发布时间:2004-11-08
摘要: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学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具有浓厚的辨学意识。依照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罗泽南对各种异学杂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辨学思想大体可以分为尊朱、辟王和批佛老三个方面,其中尊朱为其思想的基础,辟王为其思想的核心。
关键词:辨学;尊朱;辟王
儒家辨学卫道的传统由来已久,孟子“黜管晏”、“辨杨墨”素为后世理学家所称道。罗泽南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按照轻重缓急的不同,分别给予了程度或异的批判,其中对于阳明心学与佛、老之学的抨击尤为激烈。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罗泽南的辨学思想。
一、尊朱
要探讨罗泽南的辨学思想,不能不首先辨明罗氏学术的归属。学术界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钱穆的观点是:“凡罗山之学,上自孔、孟,下至周、张,非有新论奇说,而止以程朱之说说之。”①萧一山则认为罗泽南“似非专宗程朱者”②。在考察了罗氏的著作之后,笔者倾向于赞同钱说。关于儒家的历代学者,罗泽南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评述:
立万世人道之极者,其惟孔子乎!孔子,天下之至健也,运量万世不见其或息也;天下之至顺也,持载万物不见其或遗也。颜、曾见知,思、孟缵承,天经地义,昭如日星。自是而后,圣学荒芜,分离乖隔,莫知其宗。宋儒诞生,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黜近功,熄邪说,天下之士始得与闻大道之要。濂溪,圣之继者也;明道,圣之绍者也;伊川,圣之翼者也;紫阳,圣之成者也③。
把先秦诸儒——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与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说都列入正学,作为“别?邪之失”④的标准。但是与大多数理学家一样,罗泽南实质上推崇的并不是先秦诸儒,而是有宋诸儒。他认为,只要“探宋儒之精微”,自能“跻孔、孟之堂奥”,“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灿然大明”⑤。这表明罗泽南所揄扬的并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先秦诸儒,而是带有浓厚程朱色彩的孔孟学说,宋学才是他真正安身立命之所在。
对于宋儒,罗泽南也非一视同仁,他最为尊崇的显然是被其称为“圣之成者”的朱熹,以为“朱子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精微,非朱子无以发”⑥。他将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推崇备至,并且隐寓有继朱熹而挺立、起衰振弊、辨学卫道之意。
罗泽南的大部分著作,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带有十分明显的朱学印记。比如,《人极衍义》一书即为“罗君仲岳诵《太极》、《通书》之言,而得其旨要”⑦而作,该书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理解和发挥,与朱熹《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姚江学辨》辨王学与朱熹辨陆学显然更是异代同调。罗泽南在一封答友人的书信中曾透露著《姚江学辨》的原因,书云:“象山之学,已经朱子明辨,弟固未曾及,惟姚江良知之说,窃禅门之宗旨,乱吾儒之正道,虽经前人议论,而其中之似是而非者,尚未能一一剖析,故曾为明辨之。”⑧《读孟子札记》多次征引《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对朱熹的议论颇为欣赏,以为可以“补孟子言外之意”⑨。《小学韵语》是以朱熹《小学》为原本,“撮其大要”辑成,“复取古人注疏附于其下”⑩。《西铭讲义》“附于朱子《解义》之后”,与《西铭解义》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可以说,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罗泽南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与此相联系,明清两代的宗朱学者也是罗泽南称许的对象,尤其是明代的罗钦顺和清代的陆陇其。罗、陆二人都讲究学术上的正邪、是非之辨,曾激烈地抨击过陆王心学,因此得到罗泽南的特别推崇。朱熹、罗钦顺、陆陇其等人对各种异学杂说的辩驳显然对罗泽南具有一定示范与引导作用,罗氏拒斥王学与抨击佛、老,除了出于维护学术纯正的责任感外,还不免带有一些效仿先贤的意味。
二、辟王
嘉道年间,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复兴,陆王心学也出现了复苏的苗头。一些宗陆、王的学者借助程朱理学复兴之势,采取调和程、朱与陆、王的方式,努力扩大心学的影响。罗泽南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学术动向,对于尚为浅溪暗流的心学十分警惕,以为心学绝非“已毙之虎狼”。因此虽然罗泽南对陆九渊、王阳明二人的品行、事功表示肯定,承认“陆子品谊、阳明勋业,固有不可磨处”,但是为避免心学再度盛行,“废讲学以求顿悟”,危害圣道,他把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了阳明心学,其辟王思想集中体现在《姚江学辨》一书中。
罗泽南认为朱、王之异不仅在于知行观的不同,更在于心性论的迥异。正是由于王阳明对心性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才造成了其“致良知”说对朱子“格物致知”说的背离。因此,罗泽南首先对王阳明的心性论展开了条分缕析的批判。对于王阳明在心性论上与朱熹的不同,罗泽南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论述:
朱子以性为有善无恶,阳明以性为无善无恶也。朱子以性为理,心不可谓之性;阳明以心为性,吾心之灵觉即天理也。朱子以仁、义、礼、智为性之本然,阳明以仁、义、礼、智为心之表德也。此本体之所以异也。若夫善念之发,朱子以为率性,阳明则谓心体上着不得些子善念也。好善恶恶,朱子以为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阳明则谓心之本体本无一物,着意去好善恶恶又是多了这份意思也。万事万物,朱子以其理皆具于心,日用伦常各有当然之则,阳明则以事物为外来之感应,与心体无涉,以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是为揣摩测度于其外也。此大用之所以异也。
显然,朱、王之间最重大的分歧在于本体论,这也是朱、王之学互不相同的根源所在。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罗泽南开篇即将王门“四句教”抛出予以驳斥。“四句教”的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在王阳明那里主要是强调心之本体的无滞性,但是在朱熹的哲学中,“心之体”指的是性,加之王阳明也有“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的说法,那么“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也可以理解为性无善无恶。罗泽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王阳明判定为“性无善无恶”论者的。根据孟子的性善论(这也是朱熹所信奉的),他对王氏的“性无善无恶”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进而,罗泽南又批驳了王阳明“仁、义、礼、智是性之表德”的观点。根据朱熹的学说,仁、义、礼、智分别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相对应,“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因已发而有者也,表也;仁、义、礼、智,未发之中也,大本也”。王阳明以仁、义、礼、智为表德,把仁、义、礼、智看做是心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表现,这是罗泽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为若是按照这一逻辑,“则仁、义、礼、智非我固有也,是则仁、义、礼、智由外铄我也,天下之人孰有肯为仁、为义、为礼、为智者乎?天下之不仁、不义、无礼、无智者,孰肯反而为仁、义、礼、智乎?”由此可以看出,罗泽南不仅重视学理的纯正性,更关注一种学说产生以后可能带来的社会流弊,从而表现出他作为程朱理学家的本色。
在辨析了朱、王性之诸说的区别之后,罗泽南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王学的主要论题——“心即理”说。王阳明认为“心即性,性即理”,把“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并指责朱熹分心与理为二,这就难免要遭到罗泽南的攻击。依据朱熹哲学对心、性、理的定义,性即理,心绝不可以称为性,因为心不单指本体心,也具有经验心的意义,所以“心即理”绝对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命题。正如罗泽南所指出的:今夫性有善无恶者也,心有善有恶者也。曰慈祥、曰恭敬、曰裁制、曰精明,心之能顺乎理而不失者也;曰残忍、曰放肆、曰柔懦、曰昏昧,心之贼乎理而不顾者也。如果“以心与理为一”,就无法依理对恶人恶行进行责难,因为“公心是理,私心亦是理”,“乌得谓行仁者得乎理之自然,假仁者非其性之固有乎?”
朱、王之学势同水火的根源固然在于心性论的差异,但是最显著的不同却在于“格物致知”说与“致良知”说的对立,这一区别自然也是罗泽南辨析的一个主要方面。“致良知”说是王阳明结合了《大学》之“致知”与《孟子》之“良知”两个概念提出来的,认为良知是每个人不假外求、内在本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人们所要做的就是扩充自己已经意识到的良知,使良知本体全体呈露出来。基于这一理论,他对“格物致知”这一概念作出了与朱熹截然不同的解释:“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取消了格物的认识功能和意义,并将格物统于致知之下,从而完全否定了朱熹以即物穷理、扩充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格物致知”说。这是罗泽南根本无法赞同的。他指出:人之一心,莫不有本然之理,即莫不有自然之知,惟其气禀有清浊,故其知识有广狭。人之良知不过识其大略,不能洞烛其精微也。在此基础上,罗泽南又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提出了反诘:“既曰良知善即知其为善,恶即知其为恶,则良知无待于致矣。良知犹待于致,不得谓之良知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王阳明在概念诠释上的疏忽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故钱穆认为:“罗山之辨王申朱,皆确然有见,非拘拘于门户之为见也。”
宗朱学者在辟王时,总要大肆渲染王学的佛学渊源,罗泽南也是如此。《姚江学辨》开篇即以高屋建瓴之势将王学与佛学比附在一起:“昔人谓佛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吾谓阳明《传习录》、《大学问》、论学诸书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无善无恶。”从总体上将王学与佛学划一归同。随着对王学批判的深入展开,罗泽南进一步把王学的一些具体论题与佛教的经文偈语联系起来,如:“其曰理无动者,本性虚寂,善恶两无,不与物来,不随事往,即佛氏之所谓常住不动,真性如如者也。其曰常知常照者,良知之灵明炯炯,无一息不照,即佛氏之以日月灯喻法,日昱于昼,月昱于夜,灯光常昱于昼夜也。”“其以天下无心外之物,此楞严经所谓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以良知为天理,此佛氏之以知觉为性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罗泽南尽可能将王学中已经改头换面的佛家用语揭示出来,以坐实王阳明“阴实尊崇夫外氏,阳欲篡位于儒宗”的“罪名”,以便将王学彻底排斥在儒学系统之外。但问题是,不单是王阳明,即便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包括罗泽南最尊崇的朱熹,也都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一点,罗泽南一直避而不谈,他是不了解,还是根本就不想承认,尚有待于深入考察。
罗泽南对阳明心学的批判,进一步确立了程朱理学对于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对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得到一些宗程朱学者的高度赞扬。
三、批佛、老
对于佛、老,罗泽南显然是极为反对的,这从其对王学的批判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二。此外,罗泽南还有一些专论佛、老的文字,从中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其批佛、老的思想。罗泽南拒斥佛、老的态度相当坚决,以为“异端之徒不绝,圣贤之道不行”,只有“禁僧道庐寺观”,才可以实现“天下之人知正教”的理想。关于佛、老的危害,罗泽南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寂灭清净乱正道也,遗君弃亲畔人伦也,鳏居寡处绝生机也,佛阁道院竭财力也。”即淆乱圣学、背弃人伦、破坏生活与生产。对此,罗泽南分别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罗泽南还驳斥了佛教的轮回说。在佛教的生死观中承认有“鬼”的存在,罗泽南以儒家气化流行的观点反驳说:“人之魂,阳气也;魄,阴气也。阴阳之气交,则魂凝魄聚而人以生;阴阳之气判,则魂升魄降而人以死。既死之后,其气已散,安有所谓鬼者。”并对佛教的轮回说进行诘问:“信如斯言,天下之人,生生死死,止有此数,天地生物之功用,亦甚冥顽不灵矣。”这一反问,还是相当尖锐的。轮回说的流行造成了世人“日竞为淫祀,以邀福禳祸”的恶果,罗泽南特别把这一现象与儒家所称许的子孙祭祖加以区分。他认为:“子孙之精神即祖宗精神之所存,一气相传,自有可格之理。”这与朱熹所说的祭祖是为了得到祖先精神的“感格”是一致的。从中可以看出,罗泽南虽然反对人死为鬼、人死之后有魂的有神论,但是他的无神论思想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对于佛、老之教“去君臣、弃父子、离夫妇兄弟”所带来的危害,罗泽南主要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评说的。在罗泽南的诗作中有一个年轻僧人的形象,该僧“皈依佛地经廿年”,终日处于“欲依吾师亲谁养,欲事吾母身难赎”的彷徨处境。佛、老之教“使人耽空嗜寂,去离亲戚”,显然是违背人们“孩提知爱”的天性的。
罗泽南反对佛、老,不仅仅批判其谬误、揭露其危害,他还提出了禁绝佛、老之教的措施:立学校,明人伦,俾天下之人才,尽习乎大学之道。而后禁人子之丧其亲者,不得令作佛事,父母之有子者,不得度为僧尼。而又谕僧尼之还宗者,寺观中之田土,任其耕种之,贫者其父母家之宗族从而资助之,知学问者考试之。主张以教育感化为基础,辅以行政命令,标本兼治,来杜绝佛、老之教的流行。但事实上,罗泽南的禁佛、老措施也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因此感慨当权者“不出此也”。
罗泽南生活的时代正值清王朝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当时学者忧心时世,不免乞灵于学术,而由于各人的社会地位、学术背景、个人禀赋不同,所提出的思想主张也就不同。作为程朱理学家的罗泽南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极力主张辨学术之邪正的。其目的无非是要振兴早已衰微的程朱理学,通过端正学术来端正人心,进而挽救整个国家、民族的危机。罗氏的苦心孤诣,确是非比寻常,事实上也多少促进了程朱理学的复兴。但是当时思想学术界的主流是兼收并蓄,儒家内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汉学与宋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会通融合蔚然成风,甚至旁及诸子学、佛学、西学,“学术之趋势,既由分而合”,“倘坚守一家壁垒者,均不能有号召之力”,“罗山之著述,遂在若存若亡间”,出于时代的必然,“无大影响于后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①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罗山学术》,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第318、317、318页。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35页。③⑤罗泽南:《人极衍义》,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④罗泽南:《读孟子札记》卷一,《公孙上》,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⑥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二,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⑦刘蓉:《养晦堂集》卷二,《罗仲岳人极衍义序》,清光绪三年(1877)思贤讲舍本。⑧罗泽南:《罗山遗集》卷六,《答云浦书》。⑨罗泽南:《读孟子札记》卷一,《梁惠下》。⑩罗泽南:《小学韵语》,《叙》,清咸丰六年(1856)长沙刊本。罗泽南:《西铭讲义》,《叙》,清咸丰七年(1857)长沙刊本。罗泽南:《罗山遗集》卷六,《与高旭堂书》。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传习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7、115、121页。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一。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传习录上》,第15页;《传习录中》,第45页。罗泽南:《罗山遗集》卷三,《鬼神》;卷一,《有僧》;卷七,《谢星垣先生传》;卷三,《仙佛》。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1952页。
张晨怡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