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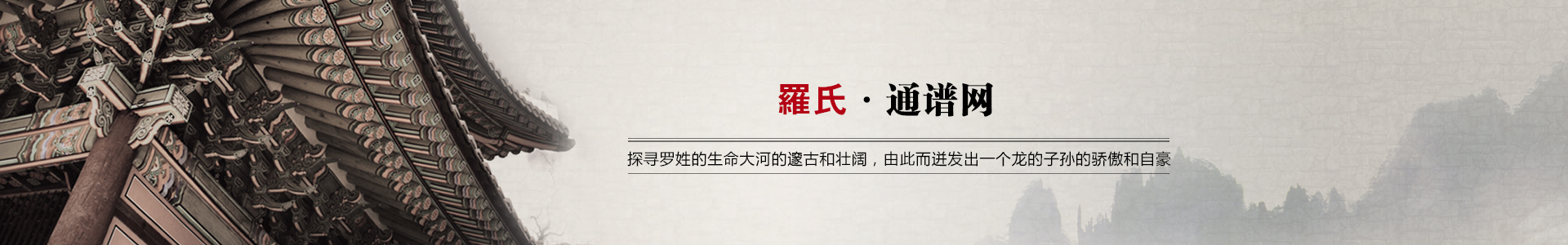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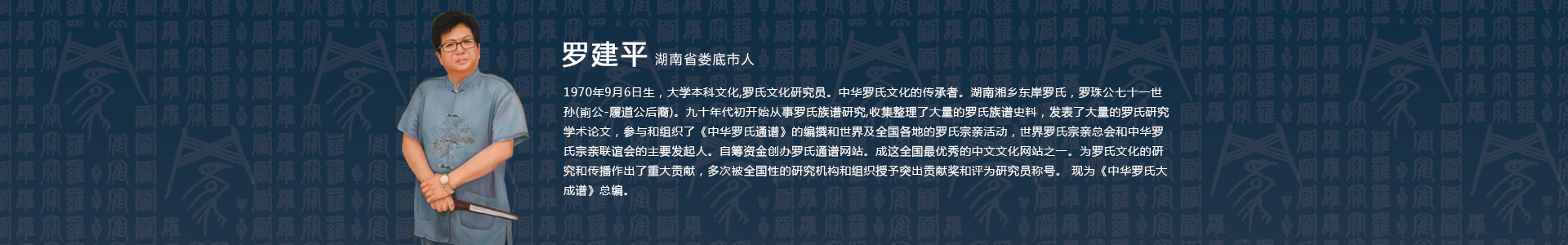
上古楚族千年大迁徙简论
龚维英 发布时间:2003-04-07
楚文化研究是中国上古文化研究的一大项,对于楚,我们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譬如,楚族的渊源及其早期迁徙史,便众说纷纭。[1]下文,拟简单谈谈楚族远古的由东而西再折向南的举族大迁移,与此同时,解决相应的有关问题。
了解了楚族早期的播迁,有些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例如,为什么楚文化具有亦夏亦夷亦苗蛮、似夏似夷似苗蛮、非夏非夷非苗蛮的特征[2],由此即可获得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
荆楚是古中国的赫赫国族,见于典籍和地下文化遗存都相当早。例如: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诗· 商颂·殷武》)
戊戍卜,佑伐芈。(《新获卜辞》三五八)
楚族原为居留黄河中下游的芈姓部落,“伐芈”即“伐楚”。[3] 《左传》隐七年和僖二年皆言及“楚丘”(一在滑县,一在曹县,时分属卫、曹二国),“这两个楚丘,当是芈氏(姓?)部落曾居于此,而以后命为国名的”[4] 。
《诗·商颂·殷武》言:“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是以知当时的荆楚(芈姓部落)旧地是殷商的近邻,故而殷商和荆楚两个国族易生冲突。在“居国南乡”后,《殷武》复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那么,可能远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殷商成汤时代,荆楚就和殷商屡屡发生武装纠纷了。
时殷大楚小,兵戎相见的结果常是殷胜楚败,楚人只好献女“和亲”,所以甲骨卜辞数见“帚(妇)楚”[5]。 先秦姓氏有严格区别,特别在战国以前,大多是女称姓,男称氏。上引“卜辞”称殷“伐芈”,可证此时的楚仍处于原始社会的母权制(母系氏族公社)时代。
附带指出,《史记》记叙上古事,往往言“姓氏”,那是太史公以秦汉之“今”而例古,是不够确切的。
但是,“和亲”仍不能制止殷商对荆楚的武装欺凌,楚族被迫西迁,据《史记·楚世家》,楚族源出于古华夏族团的颛顼高阳氏;荆楚大诗人屈原在他的著名长诗《离骚》内唱道: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伯庸即祝融,伯、祝均训“大”,庸、融相通。祝融也是华夏的宗祖之一,于古代极其煊赫。[6]可见,今所知楚文化中孕涵着颇为显著的殷(yi,即夷)文化或东夷文化因子(如祀日崇凤)。那当是荆楚阖族西过时,挟带了东夷文化同行所致。
楚族西迁当在穴熊时代。故《史记·楚世家》谓,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如学人所阐释,“荆人在殷人的压力下,多数臣服,少数逃散。”[7]我们的理解有些不同,“或在中国”即“臣服”于殷的,可能是“少数”;“或在蛮夷”即“逃散”的,可能是多数。
他们并未作鸟兽散,而是举族向西方大迁徙。
《新获卜辞》言殷商“伐芈”,当在殷武丁时代(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前后)。之后不久即到了穴熊充任大酋长时代。
此时的楚仍处在“母权制”,穴熊是女性首领(说详后)。
穴熊后经过若干时代,始有“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史记·楚世家》)。那么,到了公元前二十或二十一世纪时,楚族已迁移到周原附近,始有“鬻熊子事(周)文王”(引同前)之事,即荆楚依附姬周,充当强大的姬周的义子民族。”[8] 鬻熊率族依附姬周,有地下文物可证。1977年,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出土的周原甲骨,即有“今秋楚子来告”(H11: 83)和“楚伯迄今秋来,囟于王其侧”(H11:14)等语。
这“应在周文王迁丰以前”[9]。
迤逦到周成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楚族又由周原南迁到今湖北省境内。学人认为,熊绎“被封在楚蛮之地,才有了‘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
楚人再南下到湖南沅湘地区的,零星的开始可能在春秋早、中期,大举迁徙当在春秋而后、战国之初的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时代。“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至则相楚。……于是南平百越”(《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湖南沅湘地区在楚人进入前,正是百越族聚居之地。百越是隶属广义的苗蛮族团的大族,支系纷繁。如《楚辞·九歌》,最初即是沅湘地区的百越族祭神乐曲。后来荆楚文化浸被湖湘,《九歌》才为大诗人屈原再创作而呈现今天我们所能读到的规模。[10] 至此,楚族完成了长达千余年的大迁移,迁移的路线是由东而西再折向南:楚丘→周原→ 丹阳 →(丹淅之间)→沅湘后来,大约在楚顷襄王时代(前298──前263年),还有庄足乔(豪)入滇之举(《史记·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但规模不算太大,已属楚族迁徙的强弩之末。
二
楚族首领(酋长、子、伯、王)的名字自穴熊始,都有个“熊”字。先是后缀(如穴熊、鬻熊);自鬻熊的儿子熊丽开端,“熊”成为名字的前缀。这个变更使“熊”作为楚王族的氏而固定下来,荆楚王族芈姓熊氏。
但在穴熊时代,熊还没有成为“氏”。《史记·楚世家》详叙楚族渊源及远祖鬻熊活动大致情况,至穴熊而中断,语焉不详。穴熊以前楚祖是神人杂出,搅和了不少古神话。此正可表明,在穴熊之前的谱系,乃荆楚的精神祖先罢了。穴熊,作为有史可考的女姓大酋长,地位大抵相当于殷的简狄或周的姜女原, 是“圣处女”身份的女系祖先(高祖妣)。
不过,没有简狄、姜女原幸运,穴熊无夫生子即氏族肇源神话给佚失了。穴熊本人的姓别也使人恍忽迷离,弄不清其真面目。
母权制时代是原始社会的一个相当漫长的史前史阶段。
其时有姓无氏。《说文·女部》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因生以赐姓。”这儿讲的是“图腾感生”,“所谓民知有母,不知有父,与麋鹿共处”(《庄子·盗跖》),乃“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列子·汤问》)的结果。于是,姓成为母系民族公社时代的标识。“氏”属男姓专有,父权制替代母权制,“杂婚”(乱婚)成为逝去的旧事物,日益变成遥远的历史。这时,“氏”遂成为父系氏族公社以至奴隶制时代男权的标志。“姓”自然依旧保留,但女姓男氏严格区分,春秋时代还是这样。
以荆楚族来说,鬻熊是楚族第一个于史可考的男姓祖先。
从典籍记载他和周文王以及同时诸臣佐的关系来看,可以断言,[12] 鬻熊时代“当处于家长奴役制迈向奴隶制社会的历史阶段”[13]。“熊”作为楚王族的氏自鬻熊始。在上古时代,姓在女人的名字是作为后缀存在的,如庄姜、季芈之类。
鬻熊以氏作名字的后缀,保留了母权制以来妇女名字的风尚。
这正是男姓初获得姓尚留存旧的印痕的表现。
前言楚族自穴熊时代起,被殷族武力欺凌而西迁,司马迁目之为“中微”。《史记·楚世家》言,“或在中国,或在蛮夷”云云,“中国”指华夏族团活动的黄河中游地带,那正是楚族的祖籍及渊源所自;“蛮夷”内当然包含东夷(殷商原隶东夷,楚人有融入殷商者),更重要的指西迁南下的楚族大宗。例如姬周亦称“西夷”,所谓“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蛮指苗蛮,(《说文·虫部》)即言:“南蛮,蛇种。”蛇系氏族图腾,初无贬意。学人认为:“‘蛮’是个勤劳勇敢的美称,……蛮人是古代已具有高度文明的优秀民族之一。”[14] 由于以上诸因缘,楚王方能亢言:“我蛮夷也。”(《史记·楚世家》)那么,由荆楚族的千年大迁移历史来窥测楚文化铸夏、夷、苗蛮诸异源文化为一体的状况,我们就完全能够理解楚文化的非夏非夷非苗蛮、似夏似夷似苗蛮、亦夏亦夷亦苗蛮的显著特征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雏形形态。
现在应该谈谈穴熊为什么是女性了。
楚族氏熊源于穴熊之“熊”。虽然穴熊时代,“熊”尚未演绎成芈姓部落的“氏”。“熊”是个讹误传写之字,本来当作“今西”(古“饮”字)。在楚器名文中,楚君熊×均作“今西”。举例而言,如1993年于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坟)出土的“楚王今西章剑”,今西章即《史记·楚世家》的楚惠王熊章(前488年─前432年在位)。[15]今西章又见《曾侯乙钅甫寸》铭文。另同在楚故都寿春出土的楚器,“其中有楚王名者,计有今西肯鼎二件,今西肯簋三件,今西干心钅乔鼎、 今西干心盘各一件。
今西干心经学者考订为楚幽王熊悍;今西肯之名,一般认为即考烈王熊元。”[16] 那么,“今西”为什么讹写成“熊”? 覆按先秦典籍资料,秦惠文王时,秦人著《诅楚文》,呼唤大神巫咸而“诅楚”,詈骂楚怀王槐,书写作“熊相”(古“相”、“槐”字通)。彼时,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纵)长,至函谷关”(《史记·楚世家》)。秦人一时惶惧莫名,遂有“诅楚”之举,这是先秦时代以“熊”冠二楚君名字之始。司马迁于汉兴七十余岁之后,著作《史记》,未察于此,遂把楚君“今西 ×”均写成“熊×”了。
由此可见,穴熊本就写作“穴今西”,亦即“穴饮”。
今西,后来成为饮酒之饮的专门用语。[17]字作上“今”下“酉”;“今”是声符,“酉”酿器[18]。然而在穴熊时代,芈姓部落(楚族)尚无酿酒能力。“穴饮”,亦足可描画当时先楚部落的生活之艰苦:穴居而茹毛饮血。
我们说穴熊是一位女性大酋长, 从名“穴”可以看出。“穴”,不仅状其穴居,还是女性的标识。 初民认为“万物有灵”(Animial),一切具有性别,所以“丘陵为牡, 溪谷为牝”(《淮南子·地形训》)原始思维往往推己及物,作直观推理。初民观察人类本身既分为男女,那么,客观大千世界无不如是。故而远古时代,“天然的洞穴和凹地则用以象征女阴。”[19]古神话传说,“伊尹生于空桑”(《列子·天瑞》);《楚辞·天问》也谓:“水滨之木,得彼小子。”空桑(桑树空洞)能产子,自然等同女阴。那么,穴熊之“穴”亦为牝器无疑。 在先楚芈姓部落时代,楚文化远较殷商落后,殷商在武丁时代已有甲骨文,楚人则无。穴熊之名传于后世,自然属于口碑。“穴”作为女阴,易于传诵。文明的进步培养出人类的羞耻心。楚人尽情吸取夷、夏、苗蛮等导源文化。文明日趋昌盛,“穴熊”之“穴”的本义遂日益隐晦,竟至连穴熊本来面目也模糊不清。
这情况有点类似称母曰“妣”,妣即女阴,正是母亲的最显著特征,妣在先秦人常语里,与祖相配,祖即男根。今世俗称女阴为“尸穴”,读音犹与妣相若,[23]文明把这一切掩盖得严严实实,那么,不明穴熊的性别底蕴,就在情理之中。
以上所言,不过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24],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力争把后人有意无意掩遮楚史的幕幔拉开,拂去积尘,如是而已。楚史和楚文化需要研究的积淀太多太多,遗失的连环也很不少,力之所及,能拾起一个连环,拂去些许尘埃,就足以自慰矣。
所言当否,愿行家和读者正之。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