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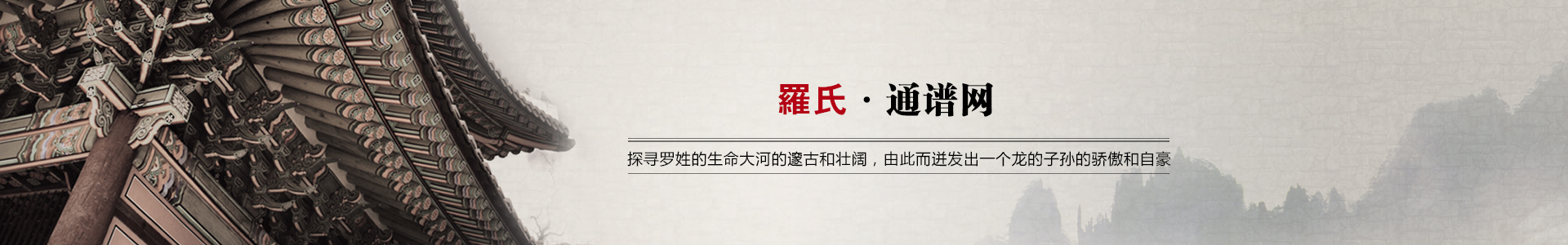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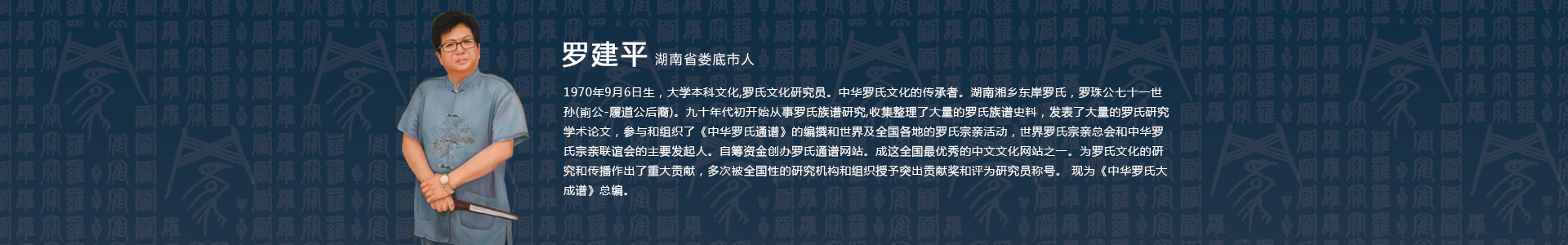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
发布时间:2003-01-20
事实与疑团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是历史事实,无可否定。个人的婚姻,本属隐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大救星”和“伟大领袖”的第一次婚姻,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大多只知道毛主席的夫人是个“电影明星”,只知道他的前妻被国民党杀害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西行漫记》出版之后,人们才知道一点讯息。正是《西行漫记》这本书,透露了斯诺记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
谈到在第一师范求学的这段生活时,毛泽东忽然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婚姻。斯诺仍然是用第一人称(一说是斯诺后来编辑出版此书时,听取了他夫人海伦的意见才改用第一人称的)记下了这段话:
“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
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罗氏正名
毛泽东的元配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韶山毛氏族谱》载:罗氏生于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日丑时),那时农户家的女儿大多没有正式的名字,她的乳名叫秀妹子,因为她在姐妹中居长,所以父母后来就叫她“一秀”或“大秀”。一秀18岁那年(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坐着花轿,吹吹打打,明媒正娶地嫁到了毛家。她的夫婿毛泽东比她小4岁,但个头比她还高。在毛家,一秀是幸福的。因为罗家也是殷实大户,一秀的父亲罗鹤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的农民。一秀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教,性格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人也生得体面丰满。嫁到毛家后,她尊敬公婆,体贴丈夫,操持家务,深得公婆喜爱。全家都随着她娘家的习惯,叫她“一秀”、“大秀”或“大妹子”,几年来日子过得温馨而又和美。
一秀的娘家罗氏家族这一支,世居韶山杨林桥(其他两支居麂子滩、鹅公坝)炉门前,与南岸毛家相隔不过六里之遥。罗鹤楼在家族中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家有二十多亩良田,又兼作谷米生意,在银田寺还有商号,再加上这种远亲关系,两人是熟识的。这就是两家结亲的背景。
罗鹤楼与其妻毛氏,生有五子五女,不幸五个儿子和次、三两女均早夭,只剩下三个女儿(罗鹤楼与继室尹氏也生过一子,亦夭亡)。而毛贻昌(即毛顺生)有三个儿子。这正是罗鹤楼选中毛家结亲的一个原因。一秀过门后,每当农忙时,毛泽东都去炉门前岳父家帮助干农活,以尽半子之劳。这使得鹤楼老人对女婿非常器重。
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
据韶山的老人们传说,毛泽东除上述常去岳父家帮工,以尽半子之劳外,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毛泽东还到岳父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的。1925年他带着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父家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应该说,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倘若他真的“不承认”这次婚姻,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又如何解释?
回过头来再看斯诺写的那段话,不难发现有两处错误:
一、“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不对。一秀嫁到毛家时,才18岁。毛泽东其时14岁。毛和斯诺谈话时,是凭记忆随口说的。或者是斯诺记错了。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人说“罗氏”比毛泽东“大五六岁”。
二、“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一秀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后来有人为了给毛泽东此话作注,说毛“拒绝和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指头”。
大概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历史原因吧,有的学者至今还把这段有着明显错误的话当做毛泽东“不承认”他的第一次婚姻的根据,去文饰他根本不存在的什么“过失”。这实在是对毛泽东本人品格的一种歪曲和亵渎。
罗氏之死和《虞美人·枕上》
罗氏是1910年春患痢疾去世的,其时还不满21岁。对于妻子的死,17岁的毛泽东心情是悲伤而又复杂的。
从9岁(1902年)开始,毛泽东开始进私塾读书。到1910年这个时候为止,他先后换了五所私塾,师从过七位有学问的先生。八年私塾教育,毛泽东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读了许多“新书”和“杂书”。17岁的毛泽东心高志远,显然,群山环抱的韶山冲已经关不住他的心了。当年他对斯诺就坦然说过:“《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这是一场守旧的父亲和奋进的儿子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它比少年毛泽东因为父亲骂他“懒惰”而闹到以跳塘投水相要挟那一次深刻得多。
当父亲正式提出要送他去湘潭米店当学徒时,毛泽东痛苦极了。对他来说,这正是他人生的十字路口。读书与学徒之争,在这个家庭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贤慧的一秀以她在娘家所受的家教和文化熏陶来看,是会从内心支持丈夫的。据现有资料,一秀患的是痢疾,在当时偏远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七天左右便可导致死亡。丧妻之痛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忧烦从两面同时向毛泽东袭来。一个17岁少年的心,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该有多么残酷!
《虞美人·枕上》应是一秀去世后不久之作。这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陆游、苏轼那些悼亡的名篇,此时必然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尽管他的文笔还略嫌稚嫩,但八年的古文功底已经足够让他作这样一次倾诉,一次呼号,一次喷发。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不止是相思之苦,也不止是怀念亡妻的愁苦,这是一个有志少年在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只有这样事关一生命运的大事,才能使青少年毛泽东心潮起伏,直如倒海翻江。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无奈。经过春夏将近半年痛苦的煎熬之后,毛泽东终于坚定了“恢复学业”的决心。他知道,对父亲硬碰是不行的,必须说服他支持自己。据说,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趁父亲外出经商即将回家的机会,把毛麓钟、毛宇居、毛岱钟、周少希等有学问的老先生都请来,待毛贻昌一到家,老先生几乎众口一词,毛贻昌毕竟也是见过世面、通达事理的人。韶山人有句俚语:没媳妇留崽不住。他内心明白,儿媳死了,儿子去意已决,再也没有什么办法留住他了,不如听从这些有学问的本家长者的意见,让他出门求学,也许儿子日后能干出胜于做米店老板的大事来。
事情这么定下来了。毛泽东胜利了。这年秋天,他背起简单的行装,走出了韶山冲,走向一片崭新的天地。故至今韶山还有老人说,倘若罗氏不死,毛泽东当年可能就走不出韶山冲———这当然只是老人们带有宿命色彩的一种街谈巷议罢了。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