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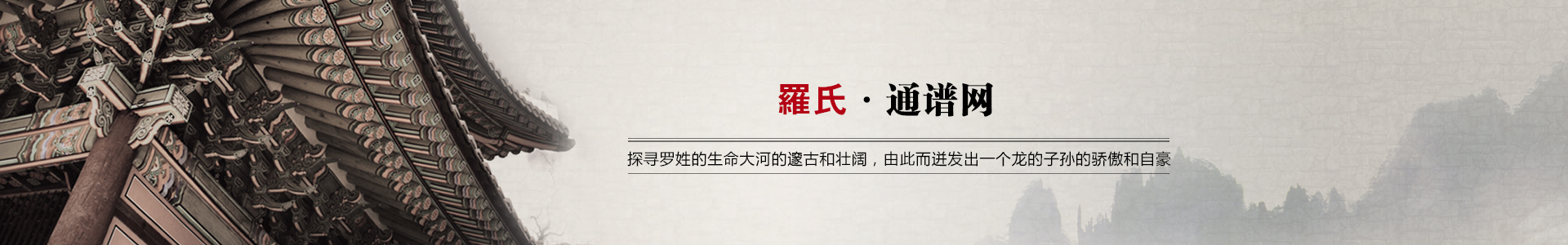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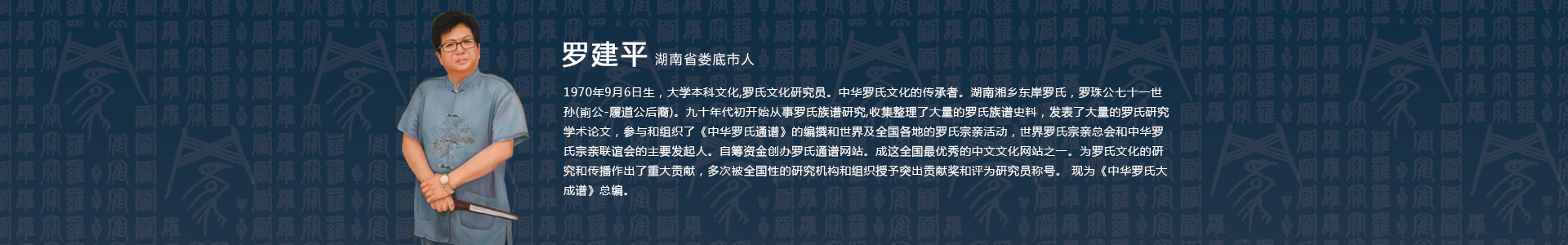
罗子国城遗址遥想
徐蔚明 发布时间:2014-10-14
记不清多少次从她的身旁走过,总想停下匆匆的脚步,去与她相识,却一次次地惧怕和敬畏,不敢走近她。春去冬来,寒来暑往。每每只是透过车窗,将她长久地打量,即使离她远远而去,也不时回头,寻觅她那远古沧桑的神秘背影。
对于她的憧憬与向往,已经积压我心头近廿载,直到今年那条江上鼓点又敲响的时节,终于按捺不住滚烫的情怀,驱车来到她的地方,去叩问和还原她,那个已经久远消失的王朝的前世今生。
近廿年的风雨、两千多年的烟云,让我伫立在她芳草萋萋的城墙上,心潮澎湃,浮想联联。
第一次听说她,是在血气方刚、怀抱理想的年代。刚刚大学毕业,进了一家工厂当技术员,同寝室一姓刘的戴眼镜的厂友,闲谈中提及了她的存在。就是这不经意的轻描淡写,却让我产生了探访她的冲动,刻骨铭心般地记着她的名字——罗子国城遗址。
人的一辈子,总揣怀着无数的冲动与向往,而真正付诸行动与实践的恐怕不是太多。两年后,我公开招聘到了市委宣传部,这种要了解汨罗山山水水、人文胜迹的冲动便更为浓烈,但依旧不敢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租了一台人力三轮车,邀上刚刚热恋中的北方女友(也是我现今的内人),从市委大院出发,直奔城西北外约5公里处的古罗子国城遗址。
出城西,要经过一条短短的老街,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似乎只有光滑零乱的条石和临街粗糙简朴的木门,诉说着这个城市的尘封与古老。而城外至罗子国城遗址那段路,则于绵绵春雨中,被出入屈原农场的车辆碾压得泥泞不堪。
三轮车人力师傅是个老者,默默地艰难地踩蹬着。我俩却全然没有顾及师傅的劳顿,也没有在乎路途的颠簸,尽情地欣赏着沿途那绿油油的一片片稻田,呼吸着和风里夹杂的春泥气息和油菜花香。
罗子国城遗址,地处汨罗江下游南岸自翁家港至马头槽之间一块广阔的土洲。1957年,湖南省博物馆曾在此进行了小规模调查与试掘,发现城址东南长约590米,西北宽400米,总面积约23.6万平方米。城址东、南、西三面护城河均保存甚好,北面城墙及西面大部城墙保存较好,墙基宽达14米,墙高3米,系用黄土分层夯筑而成。城址内试掘出土有陶鬲、盂、豆、罐等。
城址,南向是一排规整的两层红砖楼房,北面是汨罗江。放眼望去,城内城外满是一片桑蚕树,低矮的树林、丰满的树冠、茂密的枝叶,染成了绿色的海洋,其间散落的20来栋农舍,大多青瓦白墙,偶有红瓦红砖墙点缀,虽缺少苏南水乡民居那种优雅精致,却也不失湘北民居那种乡野庭院。置身其中,让人心旷神怡、无限遐想。
沿着护城河的外河机耕路上缓缓行走,南向西向的护城河上,只有一座10多米长的水泥渡漕横亘着,远远望出显得特别的抢眼。西北向的农户,大多从渡漕不宽的边缘上出入城址内外,偶尔还有农夫挑着担子或牵着黄牛悠闲地在渡槽上穿行。他们是那个古国留下来守望王朝的遗民吗?或是后迁徙而来的围垦者?这不是高不可攀的学术课题,从他们是不是姓熊或姓罗的姓氏中,就可得出断然的结论。
我们没走进城址,除了那块“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醒目的标牌令人生畏,不敢冒然踏入雷池半步。其实,城址空荡荡的一片桑林,并没有来时所想像的那样---有高大的城墙、古老的建筑、雄伟的宫殿、繁华的集市以及衣袂飘飘的罗人,自然就缺少一定要攀过渡漕的那份冲动。
却也有意外的收获,走进城外一户桑农家,破解了“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全过程。主家有两个相通的蚕房,是用一侧厢房改造的,如猪栏屋那般大小,稀密相间地摆着几排人多高的木架。木架上一层层地叠放着竹片编制的长方形条盘,每层留有约几公分的间隙,盘子里养的就是代表他们一家全年希望的春蚕。张罗着热心让我俩参观的主人,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农家嫂子,身着粉红色的花衣裳,长长的乌发被蓝色的丝巾捆扎着,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她从蚕房木架上取下一个盘子,置于堂屋前的台阶上,盘子里布满了一条条淡青色的粗壮的幼虫。挑选走幼虫吃后剩下的叶梗和排泄的少量墨绿色粪便,再把她老倌刚刚采摘回桑树顶端的新鲜嫩叶薄薄地盖上一层,然后又放回木架上,算是给蚕完成了一天的进食与打理。
她就这样,如此麻利地重复与往返着,挂满笑容的喜悦洋溢在她白净的脸上。主人看这南腔北调的我俩是那样的好奇与激动,便诗一般地轻声说道:还有几天蚕就要吐丝成蛹,然后化茧成蝶,再蝶死卵生,大约50多天就完成了它们生命的轮回和自然的使命。
那这罗子国也有生命轮回吗?她能复活吗?人又能从春蚕的自然使命中感悟到无私回报与奉献吗?遥想这些命题,我心飞翔,我心温暖。女友也在春风里沉醉得那般灿烂妩媚。这算是我第一次意义上的走近古罗城。
日月不淹,春秋代序。一晃十八年过去了。当年的毛头小伙,如今眼角爬起了浅浅的鱼尾纹,鬓角也催生了稀疏的白发。此时此刻,故地重游则是另一番心境了。
原来出城的那老街,已生长成为一个新城。那段泥泞不堪的路,则两旁挤满了外加瓷片贴墙、不锈钢围窗的楼房,间或欧式风格。而曾经送我们的那位人力三轮车师傅呢?是否还健在或是过上安康的晚年生活?我一脸茫然,不得而知。
但这两边楼房里的人却让我平生怨言,甚至捶胸顿足。你们选择这样的住居快乐吗?不能喂养鸡鸭,幼童们不能串门,还有那灰尘尾气噪声隔断着你们不敢开门,俨然就像一只只“牢笼”。当然,不止是你们,天底下的中国人如今大多还挤着向路边建房。我时常痛心、慨叹、咒诅,为何忙碌的人们不曾思考过环境与风水?只是一味的跟风,哪里有古人天人合一、座北朝南的住宅风水观。放着原来屋前有塘、屋后有树、屋旁有菜园的田园环境不要,硬是毁了原有冬暖夏凉的房子,把所有财富包括举债也要挤在路边建上这不东不西、不伦不类的楼房,以示自己的富有,或一家之主必须担当和完成的造房使命。
记得有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美国建筑大师,写过一本《建筑的永恒之道》的专著,我在翻阅中找到了答案。建筑,是自然生长的艺术,是无名的特质,是模式的语言。建筑,可以简单到人人可以担当建筑设计师,唯一的智慧就是完整地准确地遵循祖辈们留下的——关于门、窗、台、顶、墙、院、水、塘、池,以及关于阳光空气、花草树木和鸡猫鸭狗的,如何与人相处的固有思维特质和理念。由此,我想到了当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城市到乡村在一片大拆大建之中,或因开发商的逐利,或官员的干预,或业主的漠视,而丢失了祖先遗存下来的思维特质和理念,遗忘了传统建筑中共同选择的模式语言。我真担心,如今成长在城乡楼房包括城市廉租房里的孩子,未来可能面临的心性、心理和文化上的成长阴影。一句话,过去乡村里建筑的能工匠人都造汽车、飞机、原子弹去了,留下来步履匆匆的人们又只向前和“钱”看,根本没有想过家的清新、通透、阳光、生机与野趣,又何谈建筑文化和哲理意匠?难怪王澍早年就口出狂言:中国的建筑师就剩一个半,其中半个是他的导师,一个是他自己。正是这种对诗意或栖居理念的丢失,加速了各地对文化遗产的包围,使得文物环境与周边格格不入,甚至破坏文物本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罗子国城遗址又是否是这种命运?
展现在我眼前的确是另一番景象。那东西向的护城河,已被宽敞的柏油马路挤占一半,也没有呻吟与落泪,静静地无声地忍让着。那曾经的渡槽,则已被推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可以过卡车的水泥桥。那曾经的一片桑林,则被砍伐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农田,这倒也许恢复到了两千多年前的王朝风貌。那城址内的临河的星星农舍,却改成了成片的楼房,外加一个空旷没有开过工的厂房和一个打造龙舟的大型作坊。
十八年的变迁,翻天覆地。她虽抗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却抵挡不了复兴路上的现代化进程。是城址不懂得哭泣与呐喊?还是无人倾听她千苍百孔的抗诉?本应属于她的王朝与领地,任人践踏与蹂躏。
我曾在省文物局的会上,多次陈述她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大声疾呼要派专家现场指导,申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期待与屈原墓一同纳入全国大遗址保护规划。我也曾在岳阳的文物工作会上坦陈,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在我们内部取得重视和有所作为,才有可能取得领导和社会的共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古罗城遗址管理权限的变更和“国保”申报的启动,也许会迎来她新的命运。
我的思绪回到了那个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眼前浮现罗子国那悲壮的艰辛历史画卷。罗子国,是夏商时代芈部落鬻熊的一个分支,和荆楚同祖,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初,她地处大别山的河南新郑和郾城一带。这里,森林茂密、鸟类群集、人烟稀少。
相传,每于春秋两季的夜晚,鬻熊的子系们带领他的部落于山冈坦露高地上,燃起大堆篝火,周围再围以围网,那成千上万的鸟群,纷纷朝着篝火猛冲俯扑而来,都撞落在篝火的四周,大多都羽落翅折头破血流,或死或在地上挣扎。没有死伤的,则被火光照花了眼,弄得晕头转向,向四周乱窜,结果都撞入周围预设的大围网之中。篝火周围便铺起一层厚厚的鸟体,个别振翅欲飞的鸟,却被族人们用棍挥舞击落在地。往往满载而归,成为他们的佳肴。这个善于制造罗网,并用罗捕飞鸟维持季节性的生活的部落,便称为罗。大约在殷高宗武丁时,殷大肆征伐属于夏朝的残余势力——荆楚,罗是荆楚的分支,自然也遭到同样的打击,便随着荆楚部族躲避而西迁到甘肃正宁县。以后,周武王灭了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诸候纷争年代,罗突破周天子的束缚,另立王国,学楚一样战山为王。周顺势就封罗为子爵,正式成为周的附属国罗子国。以后又被周王朝讨伐,随楚国迁于湖北房县和宜城。
到了春秋初期的楚武王时代,楚凭着屈、昭、景三大贵族的力量,以及“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进取意志,继续开启拓疆征战、统一天下的历程。楚向汉水以东和以北发展势力,罗子国首当其冲。据《左传•桓公十二年》载,公元前700年,楚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楚大败。可见,当时罗子国的势力还很强大。但因楚毕竟是个大国,“其后,楚复伐罗,并其国,子孙以为氏。”也就是说约罗亡国后其子孙便由熊姓改为罗氏,或为罗侯氏。罗的遗民也被迁到楚都丹阳附近的枝江,成为楚的附庸国。
到了楚文王时,楚由丹阳迁都于郢,因罗在枝江,逼近郢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楚文王便又将罗子国迁移到被中源人称之为“南蛮之地”的南方,即地处长沙与岳阳之间的汨罗,也就是我所站的地方。
那当初罗子国的国王大臣们加上遗民们,共有多少人迁徙过来?为何选址在汨罗筑城?楚国给了她多少银两车乘?管辖的版图又有多大?她是什么时候消亡的?最后她的臣民又迁向何方?这一个个问号,曾让我长时间在史料典籍中寻觅,有些答案渐渐清晰起来,有些问号却难以找到蛛丝马迹,也许有些答案就只能在这城址以及周边相关的风物中遥想了。
城址东面有文化遗物和墓葬,从出土的陶器的质地、器形、纹饰来看,与长沙楚墓中出土的陶器风格基本一致。可知,城址的时代当属春秋战国时期。与罗子国迁此立城的历史吻合。
我走下城墙,沿着有路的地方,继续在城址内穿行,还不时弯下腰拨开一层层泥土,不断寻找她的历史深处。关于罗子国的活动范围,系麋子国的南面,在汨罗江流域一带,涵盖当今的平江县、岳阳县、沅江市、长沙县、望城县的部分区域以及湘阴县和汨罗市的全境。由于罗人的关系,把一条无名溪江改为罗水。在汨罗江北岸的楚塘乡楚南村有汨罗山,又叫罗山。屈子祠前,也有罗渊。他们皆以罗国活动地域而名。
罗子国以北,就是麋子国的活动范围。据何光岳先生的《楚源流史》介绍,到战国初,楚于今湖南一带置黔中郡,而罗、麋等附庸国宣告终结,都统辖于黔中郡。秦汉时,罗国遗民,有的留居长沙郡,有的东迁豫章郡(江西南昌)。可是,这个商、周时期的古国,在古代史料中却寥寥无几,是值得深入探讨和考证的。
昔日的高泉山,上辈们说都是墓地,只可惜已全部推平建厂筑城,现在已经成为了汨罗的城市中心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因施工而出土了一批文物,包括青铜剑、青铜戈、青铜鼎、青铜镜、玉镯等,其中有件铜剑上还有铭文。这或许从另一方面说明这里散埋着一些贵族,而且墓制时间就是战国时期。罗子国城隔江的对岸,那个叫汨罗山的,却有一片墓葬群,都是战国中晚期,其制巨大,尘封在那里,必是王侯贵族之墓了。
而新近进行的第三次文物普查,玉笥山东侧、川山城墙、磊石长山等,连续发现了商周遗址群,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汨罗曾是风水宝地,早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
思绪再一次拉回。罗子国城里曾演绎的故事,轻歌曼舞、衣袂飘飘、排箫悠扬、编钟美妙。国王的生活可就是那传说中的天堂?面对这沉睡的古城址,在常人的眼里当然是那般的平凡与普通,即使是专家也难以英雄所见略同。
我曾带领中山大学的规划团队和东南大学的张逸群等几位博士,在相距不久的日子里靠近过她。前者,对我的眉飞色舞不屑一顾,只留下一句话,一个历史遗迹而已,后者,对我的滔滔不绝如同久违的知音,反复强调一定要把她带到屈子祠、汨罗江、屈原墓的整体保护规划,形成四位一体的保护利用规划,方能打造一张完整的世界级文化名片。
试想,如果停止周边城市化进程的一切侵蚀,并有序地把这里现有的农舍迁移西边,形成一个特色的风情小镇,无论是古香古色的还是现代化的,只要代表楚文化,只要代表地域风情,自然是一大景观。再加上一个小小博物馆来陈列罗子国的故事,而罗子国城遗址只需恢复她的护城河,适度或局部显现她城池肌理就可以了,而并非要恢复她高大的城门、雄伟的宫殿以及那些轻歌曼舞的歌姬。仅此就足以让人震撼。让所有来此的看客,都可在历史与文化中、在自然与山水中得到文化的洗礼,也可为华夏那些熊姓和罗姓家族们提供慎终追远的定点,因为这里是他们是他们那家族最后终点和最先起点。即使我们难以相信百年后、千年后的这里的人流与虔诚。但让汨罗保留了真正意义上的悠久历史的文脉,形成一处精神家园。让当地人过上另一种幸福生活,则完全可以成为现实,这本身也是一项具有巨大价值的功德工程。
乌云滚滚,雷声隆隆。遥想,在宇宙聚变的大千万象中嘎然而止。我知道,这也许是一次楚游或行吟而已,不过心却顿失重负,至少圆了十八年对她的梦想。然后,我消失在风雨中,湮灭在鼓点里。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