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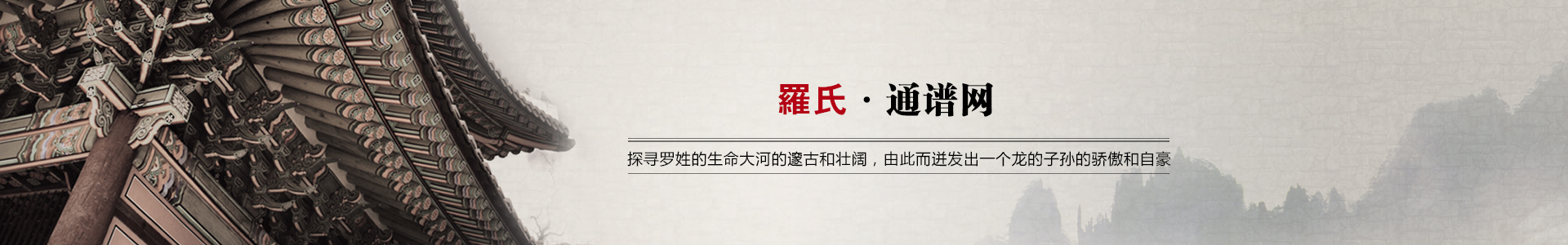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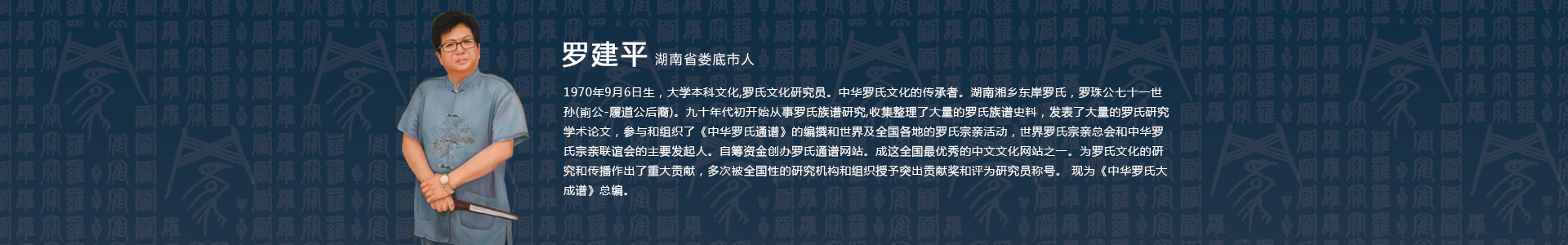
状元罗洪先绝意仕进探论
易宗礼 发布时间:2004-03-18
罗洪先,江西吉水县人,明代中朝著名的理学家。他曾一举夺得“状元”桂冠,享有当时学业领域的最高殊荣。按照封建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轨道,他可以在入朝为官的辉煌仕途上驰骋。但是,他没有这样走下去。他对自己开始追求工为之奋斗的目标,犹移不定,终于在几经周折的跌跌撞撞中,走上了绝意仕进、弃政研理的道路。本文不可能全面论述与评价罗洪先,只是就其绝意仕进的经历与心迹,作些探讨,以利剖析封建知识分子的道路,对其成败得失有所认识。
(一)
罗洪先绝意仕进,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嘉靖八年(1529),他刚获得“状元“美名时真可谓”“春风得意” 。不久。他以年轻的高科状元,被授为修撰官,率先于一批新书生加入从政队伍而登上了入朝为官的路。顺利地实现了从小企盼有朝一日发迹于政坛干一番事业的愿望。
具有满腹经纶和远大志向的罗洪先,从书少中得到许多理想境界的知识。但是,一进入具体的实际境界中,便有一种突如其来的遭遇感,前后两种”境界“区别之大犹如两重大。罗洪先一开始接触当时的朝政实际,在思想上就产生了与时宜不合的种种裂缝。他在人仕的头一年里,没有从所处的实际环境中找到渐渐适应,向理想境界推进之路,而是对眼前所见所知的现实顿生忧虑。当时,以武示朱厚照的堂弟而入继大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尚处当朝初期。他上台不久,便推出两件与以往皇帝不同的事:一是要给活着时没有做过皇帝、仅被封为兴献王的父亲朱祐杭,追尊封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以壮自己出身之高贵,而把活着时真正做了皇帝的伯父、叔父改封为皇伯、皇叔。另一件事是,按受并崇尚道士之术,听从太监崔言语的肆意鼓吹,在宫中大兴斋醮活动,整天彻夜闹得昏昏沉沉。这两件事于国民于民均无多大意义,结果却被闹得祸害 不浅。前一件即所谓大礼仪之争,不仅在上下群臣之间我争论数年,把整个朝廷武得拂拂扬扬,分成了两派。世宗借纷争不休的机会,以礼仪权威自命,重用一派,打击一派,搞得人心惶惶。而后一件事,则造成国家的权力落在一批宦官手里。他们与道士结合在一起,营私作弊,打击有为之士,迫害忠良,搞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面对当时朝廷的现实,刚入朝述职的罗洪先,既是从政新手,又是虚职闲员,如随意附和那些积极支持嘉靖皇帝的所谓“礼仪”,又觉违心负理,个人虽然受珐重用,而于国于家,亦无一用,如公开站在那些持反对意见者一边,又必将受到处罚。他感到两端均不可执,无论自己陷进那一端,都只能堕人烟雾般的政治泥淖之中,自己的政治换抱负难以施展,为安邦治国出力之愿将成为空话。于是,他断然决定告假回家,离开朝廷,避开纷争之地,视今后情况再定。
罗洪先第二次入京,是他在家闲居两年以后。嘉靖十二年(1533)诏令通知请假逾期者一律应到任述此职为皇帝、太子之教授,讲解经传史鉴等学问,虽然毫无实权,但罗洪先却乐而为之,他想以此作为手段,帮助皇帝振作精神,临朝理政,奋力振兴国家。但事实上又让他捻了。嘉请皇帝依然如故,沉心于宫内斋蘸,常常不亲理朝政,更不把讲经筵当作一回事。
他顾想的目的,仍然只是一番空洞的设想。恰巧在罗洪先求离不得理由时,其父病重。于是,他以此为由,再次告假回家,继之,父母先后去世,他居家守制,时间达六年之久。第三次入朝为官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这次朝廷授他充任左春坊左赞善之职。该职属詹事府的低级官员,自明初设立,以助 东营太子为责。至中叶以后,同中允官一样,仅为翰林院迁转之阶,实际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这样一种闲职,对于一向勤学敬业的罗洪先,无异于淹没思想,荒芜事业。因此,他深感无聊,难以自慰。当时,翰林院有一位与他同科的省元、司谏唐顺之和另一位校书赵时春,均不问出众,思维活跃,又都属闲职少事一类。罗洪先经常与他们“日相斯许”1、,慷慨激昂,好议天下大事,以至朝廷上下,国内国外,影响甚大,中外咸称他们为“奇异三翰林”。嘉靖十九年(1540年)冬天,他们共同上疏奏请明世宗,要求在即将临近的次年元旦“天下臣儒朝觐会试之期”2、让“皇太子书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3、要东宫太子临朝理政。无异于敲皇帝的脑门,打皇帝的板子,要皇帝下台。如此直刺皇帝的痛处,即便是一纸空文、乱发议论又岂能容忍,怎能不惹出大祸?当时年三十五岁的世宗,患病在身,日夜以死为惧,四方求长生不老之术,如今一听到“言储贰临朝事”4、便以为“这是料定我将大病不起”,是诅咒他病而即死,顿时勃然大怒,命即起草诏书,严辞斥责罗洪先等,并将他们除名,赶出朝午宴,削队为民。
罗洪先的这次遭遇,既冤枉又真情。说他诅咒喜靖皇帝该死,实属冤情,一个文弱书生,何以有此恶意。说他想拥皇太于当朝理政,则全是真情。在他看来,当时的嘉靖皇帝,置朝政于不顾,尽干些于国于民无益的事,又久病不愈,何以治国安天下?早日让其儿子执掌朝纲,为朱明天下带来新的生机,又有何罪?从确保明朝天下固存的角度看,罗洪先的忠心,昭然若揭,岂有罢官之理?我而其想法未免太天真幼稚,太书生意气。封建王朝是以皇帝为子的最高统治集团。皇帝以天子自居,自以为受命于天,只要活着,宝座便应永远归他,怎样辞职于天,让位于人?这个人,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是不行的。这种皇天意识,是封建君主终身制的思想基础,,岂是一道臣子的奏疏就可以改变的?这种思想基础的顽固性,既是皇帝本身为维护其神圣至高地位所固有的,也是所谓臣民都被其统治着的思想牢、笼,是封建统治赖以维护的“紧箍咒”。谁想甩开它,便有可能被弄得头痛脑胀,甚至付出生命,所以,罗洪先等人遭到除名、排斥又是不可避免的。罗洪先这次被除名导致其日后政治生涯的结束,实际上成为他走向绝意仕进的开始。
(二)
嘉靖二十年(1541)春天,罗洪先回到离别两年的家乡。他对这次本属忠心为国反遭落职之遇,心里自然很不痛快。从此,他不但“削迹城市”,5、而且终日在家,不出门户,默默无语。一个人做官时,忠于职守竟竟业业,一旦卸官失职,便大生“失落感”,无所事事了。这时的罗洪先,犹如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一时难以定夺。人生在大转折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由缓冲而决裂的过程。罗洪先要将几十年形成的科举人仕的“官念完全舍去,不是一瞬间的转念就可以完成的事情。罗洪先作为一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封建知识分子,依然以经世邦为已任。他马自己被罢官当作一个新的起点,立志还要继续为国为民作出自己的努力,不在位也谋政,此时,他年仅三十九岁,但身体却显得衰老。于是,他坚持寒暑不避地锻炼身体,同时,更加贴近实际地扩大自己学习的范围。他考图观史,从天文、地理、礼乐、典章,到河精究。对人才、吏事、国计、民情等,也十分关心,加意咨访。知者劝告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苟当其任,皆吾事也”6、可见,他当时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在为治国安邦作更全面、更扎实的准备,与此同时,他还主动自愿地为黎民百姓多做好事。足见此时他尚元“绝意仕进”之念。
从这点总观念离发,罗兴先对自己在朝廷没有谋得施展才华的官职,又遭到世宗的除名,并不感到后悔、懊恼。无法在中央任职为官,能在地方帮助作些治理整顿,为民谋福,也是治国一方、安邦一片之举,若能见效,亦利国利民。因此,他居家以后,对他方的治理极为关注,常以秋观秋毫始末着手,洞悉时弊,大胆提出自己的主张。当时江西的地方官吏知其乃状元出身,又曾为朝廷命官,在朝中有不少结交,有一定影响,因此对他也颇为敬重。每遇重大政事,特别是难为定夺之时,往往亲登其门,向他请教。罗洪先也诚恳对待,不加回避。如郡邑田赋积弊甚多,地方官员打算另选赋册,“所司以属洪先”。罗洪先深人村落、民居,精心体察民情,他经过实地调查后,建议按田亩多少定额收赋。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并实施后,“宿弊顿除”,广大百姓“欢若更生”7、又一年,江西突发水旱,灾情严重,造成大面积歉收,不少地方发生饥荒。罗洪先为此专门“移书郡邑”,得粟数千石。他又“率友人躬赈”8、送给那些家无隔夜粮的贫困百姓。罗洪先究竟在什么时候意仕进、不问政事?据史料记载:(罗洪先)“年垂五十,对时事非,乃绝意仕进。”9、是有一事实上道理的。罗洪先在五十岁以后,有两次极好的机会,要以重新任职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可作为进一步的证明。
嘉靖三十七年(1558),罗洪先五十四岁。那年七月,一向同罗洪先友好,同时被除名罢官的唐顺之,在内阁首辅严嵩的推荐下,应召返京,任兵部职方司郎中,查理蓟镇兵马。唐顺之动身述职之前,曾专门约请罗洪先与他“同出为官”。而罗洪先却毫无所动,并郑重其事地告唐顺之,说他一心“以毕志林壑为重10、不愿再返仕途。据传“顺之强之同出”11、罗洪先仍执意不肯,他还说:“天下事为之,非甲则乙,其所欲为而未能者,有公为之,何必自我?”12、唐顺之见他情真意切,实在无一同再出之意,也只好作罢。
再是三年以后,即、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有意重新起用他,并拟假边塞急需用人为由,奏请世宗启用。世宗既已批准重新启用曾被他除名的唐顺之,罗洪先有位居要职的严嵩推荐,也极有可能获得世宗的批准,得以重新入仕,又是“假边塞急需用人”,不是置于皇帝身边之职,则更有可能获准。但是·罗洪先仍然采取了力辞不受,婉言谢绝的态度,泰然置之。他在《谢严介溪相公》的信里说,对于再出仕任职这。他在《谢严介溪相公》的信里说,对于再出仕任职之念“自断已久”。久从可时起?对照“年垂五十”来看,六、七年之久是立得住的。也就是说,他除名在家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启用他的消息,原有“苟当其任”的设想,不得不化为灰尽。事过多年之后,对严嵩的邀约断然不就,当属理之所至。而严嵩收到罗洪先的谢书后,再也没有提起用之事。
(三)
罗洪先绝意仕进,既有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又有不少客观因素的驱使,自然也有其自身的起主导作用的内在因素,我以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罗洪先“自幼端重,不为嬉弄”13、性情特殊,喜爱孤独。他“年五岁,梦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为梦,呼曰:汝来者皆在吾梦中,尚自攘攘何耶?”14、幼儿时期梦幻一类的灵性,固然不能说明与他后来无意仕进有多少直接联系,但就一个人的特性形成过程而言,则是他独有个性的最初萌发,最爱戏弄奔闹的少年时期,他却有“常敛目端坐”的惯15、是他特有个性的继续展开。他青年时期那种勤奋好学精神,常使睹其颜貌者惊服,“一日读罢严经,得反闻之旨,遂觉此身太虚,视听误人禅耶?”16、这是他极端专注、神往于读阅的特有个性的勃然发展。他踏入仕途的十多年间,每每与时局、政见不合,在“三翰林‘之间”日相斯许的侃侃阔议导致除名,是他特有个性的发展高潮。除名以后近二十年间,守静苦读,经常在读书人中论议不休,甚至射进深山石洞去“习静”,使自己特有个性进入“绝顶”阶段。罗洪先具有的突出开赋与其特殊、孤僻个性在后天的结合与发展,构成他时局发展不相融合,离实际运用的要求愈远。这是他本身铸就而最终走向“绝意仕进”的基本原因。
二、罗洪先生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封建进士之家,父亲名循,进士,任过坟方知府等职,颇多功绩。罗洪行作为“孤子”从小受到父母的倚重与酷爱,爱到家庭严格而又特殊的重德敬业教育。其父在外地做官时,还将他带在身边,进行修善自身的“小化”教育,希望日后施“大化”于人。罗循在江苏任知府时,曾过一庵,接“流尸葬之”17、即抓住这一具体“行德”之举,让罗洪先耳闻目睹,而且从此从“念庵”作为罗洪先的别、号,让儿子保持“奇行厚德”。罗洪先开始从师受业教育时,对“不优”成名的仰慕与追求,几乎到了痼疾成癖的程度。正德九年(1514),罗洪先年仅十一岁,听说罗伦是个状元,很有学问,廷试对答,对策万言,直斥时弊,名震都下,他便 慨然仰慕罗伦之学问与为人·立志于“圣贤”之学,做个象罗伦一样的人。正德十三年(1518)罗洪先十五岁,听说王阳明在赣州讲学,心即向往敬仰,“遂卑视举子业”18、还向父亲提出要前往实地拜师受业,其父以他年幼体弱为由阻止,未能如愿。后来改拜同乡李中为师。李中,正德九年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他为官清廉,不畏强暴,后弃官回家讲学,学者尊称谷丰先生。罗洪先孜孜不倦,一学几年,认真习研,苦行不止。在出仕期间以及被除名后二十年里,一直同当时的理不名家,过从甚密,他同聂豹、欧阳德、邹守益等理学家,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习,为会讲学,从小有“志于圣贤之学”的兴趣愈来愈浓,而同仕道却越来越疏无。这些,不断向学得型人才铺垫的基石,是他工于理研,拙于为官,最后绝意仕进的必然因素。
三、罗洪先五十岁以后拒绝出仕的直接原因,是他特别不佳的健康状况。正如他在《谢严介溪相公》信中所说的那样:“某福缘极浅,早婴疾痰,放斥以来,加之多故,不善摄取,衰困病增。今年才五十七耳。齿半落,发已尽白,动作稍勤,痰火坌发,旋至眩晕,非独自觉无能有为,即交游与闾里莫不相对诧惜。盖禀受至薄,理数有限,气萎智短,百务妨驰,纵在任职,亦必仰钧力营护脱解,求便其私,矧坐罪戾,适足藏拙,安敢尚有希冀。此念自断已久。不敢辄以闻者,自知谋身之鄙计,不足以称为国之公心故也”19、其中较为详细地描写他当时身体状况,固然不能排除以身体不邓作托词的可能,但从其“逼真”的程度看,齿落、眩、晕、坌痰、气萎等,如此“糟透了”的身体,若再离乡背井、赴外地做官,必然力不从心,也是显而易见。事实上,从他发出这封信以后不过四年,罗洪先便告离人世,足可证实其当时健康之“糟”是没有疑问的。
四、罗洪先谦逊谨慎,以人为镜明得失,注意从他人身上戒自己,责已求严。他得知唐顺之启用后的议论,便感到自己若再出仕,也必然非难增多,不堪重负,这也是他绝意仕进的深层原因。从唐颇之再用到严嵩荐他,中间经历三年,这三年是他绝意仕进之念加深的三年。他在《谢严介溪相公》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明他思想深处这所含:“往岁,荆川特受深知,破格拔用。凡平日深愿于荆川而不可必者,遂得之一旦,岂私荆川哉?彼诚足以任之也,某病且衰矣,所欲为而未能者,彼诚任之,即比于自效可也,岂必尽出于我哉!且荆川学识才力一出,犹不免人言,如尊谕所云,至烦向人指其议论,注措为之解释。有如某者,议论注措,索出其下远甚,则其招尤集垢,当复何若,又将何解于人言哉。”20、荆川即唐顺之,所谓如尊谕所云,即严嵩约他重新出任时,曾表时他愿帮助他说话,就象唐顺之出任后有人议论,他也“注措为之解释”一样。这里,不管严嵩出于何意要预先道及愿为“保护伞”的话,但罗洪先很清楚,虽然 学业上,他比唐顺之名气大,但论为官的实际能力与气度、乃至交友等方面,却要略逊一筹,既然如唐顺之的再出,都有微词、斥语,若他再出不可避免还会引来攻击,怕是更加难以招架,这的确道出了飘逸在他思想深处的云雾。一个原本仕途坎坷,政治上无所建树,在离开政坛近二十年之久,且年近花甲的老人,又那么体弱多病,若再度入仕,怎能胜任?又,岂能不招尤集垢?从这点上说,罗洪先的心愿是诚恳的。当然,罗洪先也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却一字未提,对这以前早已开始于理学研究,将晚年的事业放在做学问上却“甄士隐”去。这也许同他的谦逊品质有关。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