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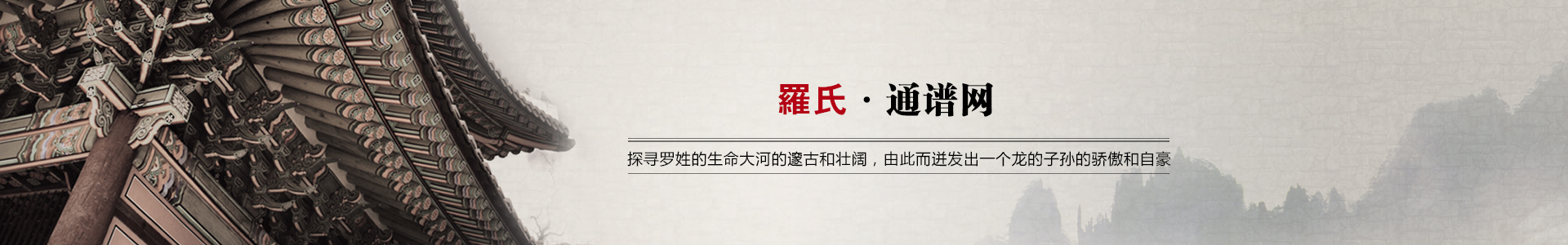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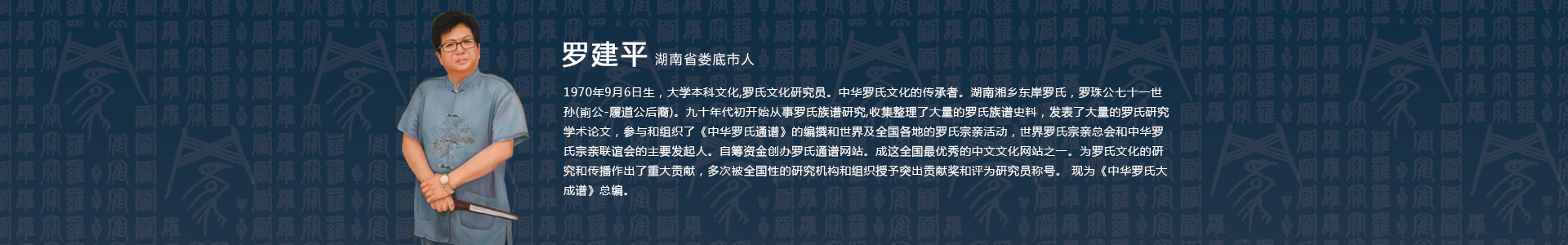
从《遵尧录》看罗从彦的政治思想
常建华 发布时间:2004-12-21
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宋南剑(今福建沙县)人,世称豫章先生,谥文质。杨时(世称龟山先生,1053-1135)曾先后师事程颢、程颐二程,得传濂洛周敦颐理学,罗从彦则是杨时的学生,罗从彦又传学于李桐(世称延平先生,1093-1163),再传理学集大成的朱熹,所以罗从彦是理学传播史上的重要人物,罗从彦是一位思想家。在元人脱脱等撰《宋史》中,罗从彦入“道学传”,可见古人对罗从彦思想的重视。
流传至今的罗从彦著述,只有十七卷的《豫章文集》,而《豫章文集》的主要内容是第2-9卷的《遵尧录》。《遵尧录》四万余言,是罗从彦编辑宋代君臣事迹加以议论的著作,靖康元年(1126)成书,拟献朝廷,会国难不果。所以《遵尧录》是表达罗从彦政治思想的著作,在现有资料的前提下,从《遵尧录》探讨罗从彦政治思想应当成为罗从彦研究的基本问题。虽然今人对罗从彦的政治思想有所论述,但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一
《遵尧录》篇首有罗从彦自序,首先论述了写作该书的动机。他说:“尧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宋朝一祖开基,三宗绍述,纪纲法度“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在太平兴国初年,太宗曾对宰相说:“朕嗣守基业,边防事大,万机至重,当悉依先朝旧规,无得改易。”仁宗见东封、西祀及修五清宫等过侈,告诫自己:“如此之事,朕当戒之。”罗从彦认为这“二圣”是“知所以绍述者”,所以太宗之世无复更张,终仁宗之世一于恭俭。他继续指出,至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功利之说杂然並陈,徽宗宣和末年遂召金人犯阙之变。今皇帝受禅登基,遭遇金兵威胁的时难。剗除熙丰弊法(指王安石变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為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有人说王安石的影响还在,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火。罗从彦说自己正是担心此点,仿唐吴兢作《贞观政要录》、本朝石介《圣政录》,“因採祖宗故事,四圣所行可以闓今传后者,以事相比,类纂录之,历三季而书成,名曰:圣宋遵尧录。” 罗从彦在国家内忧外患当头之时,为了拯救国家用三个季度即9个月辑录本朝历史写成该书。根据序言结尾所署日期“靖康丙午十月”与序中“今皇帝受禅”之句判断,《遵尧录》的写作开始于靖康元年(丙午,1126)正月,至十月成书,罗从彦打算把《遵尧录》献给刚登基的新皇帝钦宗,供皇帝治国参考。
接着,罗从彦介绍了《遵尧录》的编纂方法。他说“其间事之至当而理之可久者,则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则‘释’以发之;以今准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即对于朝廷所行合理可以持久的事情重新提出,对于朝廷所行可以持久而意义不明确的事情阐释,对于朝廷所行不合古代圣贤要求的加以“辨微”。此外,又“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颢共十人,择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其后”。如此,“创始开基之事,庙谟雄断,仁心仁闻,则于其君,见之袭太平之基业,守格法行故事竭尽公忠;则於其臣,见之爰及熙丰之弊,卒归于道”。达到规劝皇帝按照“祖宗故事“竭尽公忠”、大臣总结“熙丰之弊”“归于道”的目的。
最后,表达了罗从彦的愿望:“不久朝廷清明,金人宾伏,且当有以来天下之言,辄纪岁月以俟采择。”
综上所述,《遵尧录》的主旨是以“祖宗故事”与名相先儒的事迹告诫君臣继承传统,以弥补王安石新法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从而面对金兵的南侵。
下面,我们具体介绍《遵尧录》。该书共计八个部分,前四部分分别论述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位皇帝;后四部分论述贤相名臣,其中第五部分论述李沆、寇准、王旦、王曾,第六部分论述杜衍、韩琦、范忠淹、富弼,第七部分论述司马光、程灏,最后一部分为“别录”,有“司马光论王安石”、“陈王+雚论蔡京”。显然,别录的形式有所不同,采取人物评论的方式,以表达对王安石与蔡京的不满。
《遵尧录》各部分的编排形式一致,都是先介绍人物的言行,然后发表罗从彦的议论。这些议论又分两种类型;一是“臣从彦释”,即解释人物的言行,共计32条;二是“臣从彦辨微曰”,对人物的言行发表自己的见解,多持批评或保留的态度,共计24条。值得注意的是,“臣从彦辨微曰”24条都出现在论述皇帝的前四部分,这是因为罗从彦在此主要就皇帝的治国与君臣关系阐述自己的看法,也应当是罗从彦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
《遵尧录》是钦宗靖康元年成书的,这时北宋政权已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九位皇帝,然而《遵尧录》论述的皇帝只有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前四位,表明罗从彦只是认可这些皇帝的政治成就,认为他们确立了宋朝的基本制度。希望钦宗等后世帝王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为典范,治国安天下。因此,《遵尧录》的主旨是论述“祖宗故事”,也可以说是论述“祖宗法度”、“祖宗家法”,目的是为了法祖。
罗从彦上书谈“祖宗故事”在当时不是偶然的,宋朝还有不少士大夫建议遵守“祖宗家法”。北宋哲宗时期,吕大防有《进祖宗家法札子》认为:“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他总结的“祖宗家法”主要有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共八项。还说:“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田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认为尽行家法,足以治理天下。钦宗初年李纲也请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北宋中后期的这些上书,希望依靠祖宗家法完成守成大业。从家法形成过程来看,主要是创业君主和守成明君留下的方针政策。如钦宗时李光请求讨论“祖宗故事”以守成,强调的是“太祖太宗以英文烈武戡定祸乱,创业垂统,规模宏远矣。五宗(华按:指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守成以至道君,上皇继述之美,天下治安几二百年。”建议“绍复祖宗故事”。南宋高宗时,赵元镇上书说:“国家之有天下也,始以太祖之武,建创业垂统之功;继以仁宗之仁,得持盈守成之道,致治之术,先后相成,垂裕后昆,为法万世。”他更强调太祖与仁宗创立家法的重要性,建议高宗法太祖之武与仁宗之仁,把祖宗之法作为家法。比较而言,罗从彦也最服膺太祖、仁宗“二圣”,不过他也论述了太宗、真宗的事迹。
今人对宋代祖宗家法的研究也值得注意。有学者指出:“宋代经过太祖、太宗两朝,法制基本已完善,形成有宋后世所习称的‘祖宗法制’、‘祖宗家法’。在治国成规上,皇帝握立法与否决之权,宰辅理事,握行政之权,“共治天下”,是所谓成法。”更有学者就如何看待“祖宗家法”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北宋初很快形成了一整套权力制约体系,并成为所谓“祖宗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研究者将死守祖宗家法视为造成北宋积弱不振直至最后灭亡的重要原因。其实在宋朝的三大基本国策即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与祖宗家法之间不能划等号。对于祖宗家法,应作具体分析。形成于宋太宗两次北伐燕云失败之后的守内虚外国策当然应当加以否定,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国策仅适应北宋初期的形势,不能视为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此后理当及时加以调整。至于权力制约体系,既有造成政府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消极作用,又有防止权力恶性膨胀、减缓腐败蔓延速度的积极意义。从总体上说,北宋亡国并非死守,反倒是放弃作为祖宗家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力制约体系所致。祖宗家法应当受到历史的肯定。
结合古今学者的论述,可见“祖宗家法”在宋史中的重要性,
《宋史》罗从彦本传引述罗从彦思想时,分为“论治”、“论士行”两部分。“论治”部分反映出罗从彦的政治思想。其内容是:
“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孙世守文、武、成、康之遗绪,虽至今存可也。”
又曰:“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乱。”
又曰:“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奸,则外必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泚之叛。”
这三段话,均见于罗从彦的《议论要语》,核心是说维持国家稳定的关键是遵守祖宗法度,朝廷用人应当用忧国忧民的“君子”,而不是歌颂盛世的“小人”,国家的安危系之于朝廷内部。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罗从彦思想,可谓切中要害。《宋史》评论罗从彦“议论醇正”,说明他的思想非常符合儒家正统观念。
二
下面根据自己的体会,具体探讨《遵尧录》所体现的罗从彦政治思想。在罗从彦总结的“祖宗故事”当中,比较强调君臣之道,重视皇帝与宰相的修养以及二者的关系,试图建立儒家正统思想的稳定的意识形态。
在为君之道方面。罗从彦认为君道在于心正,他说:“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则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P655—65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豫章文集》页数,下同)帝王的嗜好当淡然无欲,他说:“太宗语李至曰:‘人君当淡然无欲,不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邪无自入焉。’可谓善矣。”(P663)纳谏是君王的美德,他指出:保申之能谏,楚文王之能从,其事见于刘向《说苑》,“太宗提出言之,取其大意,非特施于一已与子孙也,且以示天下后世,使知人君纳谏之美,有至于此也。”(P664)又说:“太宗时内庭给事不过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也。武程疏远小臣妄陈狂瞽,帝不罪之,以来天下之忠言,可谓善矣。”(P666)君主应存徳意,他说:“仁宗承平之久,纪纲不振,盖因循积习之弊耳。然能为太平天子四十二年,民到于今称之,以徳意存焉故也。况徳意既孚於民而纪纲又明,则其遗后代宜如何耶。”(P687)批评以非理之说佐治,他说:“今其言曰皇后梦羽衣数百人从一仙官自空而下,曰此托生于夫人,则非理矣。”(P688)天子所为,要须有以风动天下。他说:“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仁言仁声有以异乎,曰仁言为政者,道其所为仁声,民所称道,此不可不知也。夫天子所为,要须有以风动天下,如汉光武起循吏卓茂而以太傅处之,魏以毛玠为尚书,唐以杨绾为宰相是也。区区命令,非所以感人也,彼汉唐之君何足道哉。然一时之间所为合理尚足以感动,况以尧舜之道革易天下者乎。”(P689)
君主赏罚应劝功惩罪。他说:“赏罚者人主之大柄也,赏所以劝劝功,罚所以惩罪,天下共之。太祖时臣僚中有功当进官,此天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进,此蔽于私者也。”(657)君主赐予应有可称。他说:“賜予虽出于人君之仁,要受其赐必有以称之可也。”(P658)察州县官吏善恶关乎为治,他说:“察州县官吏善恶自有常典,又时遣专使辨其能否疲软苛刻以闻,而褒黜之,足以为治矣。”(P679)君王应能够辨别君子小人,否则为旷职,他说:“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者,以其举元凱去四凶也。夫君子与小人相为消长,虽文明之世不能,必天下无小人,虽乱世不能无君子,唯能辨之,使各当其分,此南面之事,而天子之所守者也。故进君子远小人,则为宜其职,忠佞杂处小人在位,则是旷职矣。天子而旷其职,则乱亡而已矣。”(P 711)同时也认为用人区分善恶不可太察。(P 708)
为臣之道方面。认为大臣应“兼善泽民,以天下为心,不忘王室”。(P707)主张大臣要善于规谏君主,他说:“古者忠臣之事君也,造次不忘纳君于善,有剪桐之戏者,则随事箴规;违养生之戒者,则即时戒正”。(P657—658)又说:“杨亿文章擅天下,真宗使处翰林,则是亿有文章而帝有亿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以亿之才艺,其处翰林之日非不久也,不能纳其君以文章融于性与天道,使间言得行,何所归咎耶。”(P679)批评李沆不能谏君之失。(P692)主张乐与人为善,团结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他说:“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已,而恶人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以出乎众为心,则以其不大故也,唯大为能有容,善者共说之,不善者共改之,宜无彼己之异,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若衍存心至公,而乐与人为善,不以必出于己为胜,其舜禹之徒与。”(P703)他以宰相和台谏官为例,希望大臣终于职守,敢于建言。他说:“凡为天下国家者,其安危治乱,是非得失,必有至当之论,至正之理,而宰相行之,台谏言之,其总一也。至于宰相或取充位,则台谏不可以无言,台谏或非其人,则宰相不得以缄黙,趋于至当而已矣。”(P 704)主张同僚当中当以有才者为重,如此有利于国家。(P 702)
强调朝廷的用人之道。用人不可过分挑剔。他指出:“真宗尝谓宰相曰:‘朕于庶官中求其才干者尚多有之,若以徳行則罕见其人矣。’夫徳行之门必有忠孝,未有徳不足而忠孝能全者也。真宗尝谓宰相曰:‘臣僚中有被谤言达朕听者,咨之于众,似得其实。’然为臣为子鮮有无过之人,但能改过知非即为善也,况朝廷不以一眚废人终身之用乎。”(P673)强调用人之策。以冦准为例,说明“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贤不可责备。”(P695)又主张“用人以徳器為先,才大而徳不足只为累耳”。(P695)
至于君臣关系。要求君主对大臣有礼,大臣知廉耻,他说:“古者,君臣之间礼义廉耻而已矣。上知有礼而不敢慢其臣,而下知廉耻以事其君,上下交修,则天下不足为也。”(P 657)批评君主过分专制,不相信大臣。他说:“真宗咸平中,命宰相枢宻陈御边之计,帝总揽而裁定之,他日对便殿内出阵图,谕之曰:‘朕虽经划如此,以付诸将,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审观可否,更同商议。’而李沆等以为尽合机宜,此于制胜一时之策,可谓善矣。然非常行之道也,自古朝廷之事可付之相,边事付之将,茍自中制之,立为阵图以授之,内外不相及,必有失机会者矣。古人云阃外之事将军主之,此最为知言也。”(P671)以皇帝不相信宰相王旦事例,指出君臣一体,“人主于宰相疑则勿任,任则勿疑。”(P697)有学者指出,徽宗同其列祖列宗一样,始终将最后决定权和宰相任免权紧握在手。他在位26年,更换宰相13人,宰相任期一般极短,大多不到两年。其中,刘正夫任期最短,仅7个月;何执中、王黼任期较长,也无非6年左右。罗从彦此言实属有所感而发。
君臣应合心同謀,他说:“小人之权幸可畏也久矣,以仁宗之英明急于图治,晏殊为相,群贤在朝,天下拭目以望太平,而富范等各条具其事,以时所宜先者方施行之,欧阳修又以天子更张政事,忧悯元元,而劳心求治之意,载于制书,以讽晓训敕在位者,可谓一时之良。而衅於谗间,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与合心同谋,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断之,为之不暴,而持之已久,故小人不得以措其私,权幸不得以揺其成。若庆历之事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君臣之间毋乃有未至耶,致治之难,古今之通患也,可胜咤哉。”(P690)
特别是关于皇帝与宰相的关系方面。认为君主应知命相,他说:“太宗之命吕端也,说者谓宰相之任在乎登进贤才,黜远庸佞,而总其纲目,万事自理,故曰天子择宰相,宰相择百官,非才之人不可虚授,其言是已。若太宗者,其知所以命相者欤。”(P660)
宰相应当进贤退不肖,他说:“古者进退人臣自有道,而宰相者乃辅天子以进贤退不肖者也,不可不谨也。”(P658)又说:“宰相之职在于进贤退不肖,古之人有举之至于同朝而人不以为徳,有废黜之终其身而人不以为怨者,合于至公故也。故举一贤使天下之人知如是者皆可勉,去一不肖使天下之人知如是者皆可惩,无非教也。”(P700)用人当重人望,他说:“王旦章圣时在中书最久,每进用朝士必先望实,茍人望未孚,则虽告之曰某人才、某人贤不骤进也,此真救弊之良图也。曽之当国也,遵行其言,人皆心服,非已行之验故耶。”(P699)宰相应出于公心,他说:“宰相以天下为己任者也,推公心由直道,务使下情通以防壅蔽,不亦善乎。而恶闻忠言则其人可知己。仁宗时执政者禁越职言事,弼因论日食请除其禁,此亦尧舜明四目达四聪之意,而治乱之机也。”(P 709)
立后对于君主与国家很重要,罗氏也有所论述。特认为皇后不可改易,指出:“古者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徳,终身不变者也。礼有七出,为大夫以下者言之,天子无废后之文,诸俟无废夫人之事,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采择之法在审其初而已,所以防色欲窒谗间杜僣乱治乱禍福之机在于此矣。仁宗时郭后以无子愿避后位入道,理之所不可者也。故仲淹等争之,至伏阁论列,当时执政之人不知以尧舜待其君,乃引其君使蹈汉唐弊法,可胜惜哉。”(P688—689)又认为皇帝亡后不可复娶。他说:“男女之配终身不变者也,故礼天子诸侯不再娶,说者谓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亡可以攝治,故无再娶之礼。唐啖氏亦曰古者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则次妃攝行内事,无再娶之文。故春秋之法,仲子不得为夫人,由是言之,则天子可知矣。明道中郭后入道,宰相等劝帝复娶曹后,其累盛徳,盖不特章献服未除也。后之为人君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P689)太后临朝之事,皆非治世典礼也。他说:“周成王嗣位之初,攝政者周公而已,炎汉以来乃有太后临朝之事,而后世袭其例,遂以两宫称之。或曰二圣。皆非治世典礼也。”(P699)
罗从彦尊奉尧舜之道,实际上儒家三代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因此罗从彦强调确立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他主张尊奉儒学正统,屏弃佛道。首先主张道术在于知有圣人,他指出:“道术不明久矣,汉兴有盖公者治黄老,曹参师之,其言曰治道贵清浄,而民自定,是也。然其相汉也不过遵何之法,勿失而已矣。非圣人之诚也,圣人之诚,感无不通,故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其感人也,不见声色而其应之也捷於影响,此尧舜孔子之道也。”(P667)君主尊孔为知本。他指出:“唐时诏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独孔子用王者事,以门人为配,自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荐祭不敢少忽者,非以其为万代之法故耶。行之未几,而浅于学者智不及此,乃请东揖,以杀太重,历朝循而不改。逮及我宋,章圣皇帝之幸曲阜也,奋独见之明,特展拜以表严师崇儒之意,徳之盛者也。若章圣皇帝,可谓知所本矣。古者帝王称号,因时而已,非徳有优劣也。唐明皇既追封先圣为王,袭其旧号可也。加之以帝号而褒崇之亦可也,顾时君所欲何如耳。”(P675—676)
他批评太宗景慕老子学说,指出:“老氏芻狗之说,取其无情而已,以圣人之神化言之,则不见其诚,以万物化生言之,则不见其感,世有为孔老之说者,岂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耶。夫鼔万物不与圣人同忧者,天之道也,圣人則不免有忧矣。若使百姓与万物等,而一以芻狗视之,則亦何忧之有,故老氏之学大者天之,则诋訾尧舜不屑世务,其下流為申韩者有之矣。”(P668)还从立人之道在于仁与义方面,认为应戒老子之说。他指出:“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体也,义用也,行而宜之之谓也。所谓智者知此二者而已。及其行之也,若禹治水,然行其所无事而已矣。尧舜之治不出乎此。自周道衰,洙泗之教未作,而世所谓智者不然,机变之巧杂然四出,故鸟乱于上,魚论于下,人乱于中,此老氏之所以戒也,非公天下者之言也。”(P667)不仅批评道家,还认为佛学不合尧舜孔子之道。他说:“佛氏之学端有悟入处,其言近理,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窥,太宗之言是已。然绝乎人伦,外乎世务,非尧舜孔子之道也。夫治已治人,其究一也。”(P668—669)因此,君主应远于佛仙之学。他说:“圣人尽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盖欲天下皆至於圣人。佛仙之学,不然是二之也。故君子不贵也”。(P669)
在儒学经典中,罗从彦特别看中《春秋》与《中庸》。他说:“愚闻之师曰:‘《春秋》之书,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自周道衰,圣人虑后世圣王不作,而大道遂墜也,故作此一书,若语颜渊为邦之问是也。此书乃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也。”(P684)又说:“《中庸》之书,此圣学之渊源,六经之奥旨者也。天下大治,天其或者无乃有意斯文,將以岂悟天下后世故耶。”(P684—685)还指出:“《中庸》之书,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中者,天下之大本,庸者天下之定理,故以名篇。此圣学之渊源,六经之奥旨者也。汉唐之间读之者非无其人,然而知其味者鮮矣。自仁祖发之,以其书赐及第进士王尧臣等,厥今遂有知之者,昔者尧舜相授不越乎此,而天下大治,天其或者无乃有意斯文,将以岂悟天下后世故耶。”(P684—685)在尖锐的民族斗争面前,他也认为帝王应知霸王之道,他说:“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徳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善乎孟子之言,昔孔子没孟子继之,惟孟子为知霸王者也。夫学至于颜孟,則王道其几之矣。故知圣人之学者然后可与语,王道不知,圣人之学不可与语也。不知圣人之学,骤而语之,曰此霸道也,此王道也,必惑而不信矣。圣人不作自,炎汉以来有可称者莫不杂以霸道,汉宣之言是也。若唐贞观中海内康宁,帝曰:‘此魏徴劝我行仁义之效也。’盖亦假之者也。神宗時以司马光之学犹误为之说,又况其下者乎。然则霸王之道要须胸中灼然,当时宰相未必能知也。”(P681—682)
罗从彦既然强调儒家政治思想,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儒家治国主张自然也是他看中的。
罗从彦有民本的思想。太祖建隆初扬泗饥民多死者,沈伦请发军储以贷之,罗从彦认为这是“知本”,而太祖则“善听言”。罗从彦指出:“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也。民之所恃以为养者,以有食也。所恃以为安者,以有兵也。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昔孟柯氏以民为贵,贵邦本也。故有民而后有食,有食而后有兵。自子贡问政孔子所答观之,则先后重轻可知矣。”(P 650页)也主张君主应勤政。真宗曾出《勤政论》以示群臣,宰相更请出示朝廷。罗从彦赞赏勤政。他说:“帝自咸平初以至祥符,躬亲庶政十有五年,而在京诸司,每以常行事务诣便殿取裁,事无大小,一决宸衷,故孙冕、王嗣宗等得以言之。……帝既以冕奏,颇知大体。又降诏以奖谕嗣宗,可谓能听言矣。而宰相乃请以《勤政论》出示朝堂,孔子所谓将顺者岂其然耶。”(P677—678)还认为事天之礼不可阙。他指出:“古者岁一郊,牲用茧栗,噐用陶匏,无甚繁费,取其恭誠而已。今三岁一有事焉,已非古典,若赏赐士卒,乃太祖一时之命,后因以为例,议者犹欲不给新兵以渐去之,而两府以下皆赐金帛何耶,王嗣宗知财用数目而已,固不足与议礼。蒙正名臣也,谓前代停郊谒庙,盖因灾沴,今无故罢禋祀典礼无据,且水旱无常,不幸有故,用前代故事可乎。善乎,真宗之能守也,不计郊壇一日之费,事天之礼不可阙也,若士卒赏赐可革,革之;两府以下金帛可削,削之。一主于恭诚,孰曰不可。”(P678)基于敬天思想,认为天书之降非天理,他说:“昔尧舜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恐人神杂糅故也。使天书之降,果真有之,盖已非尧舜之治矣。以理考之,穹然黙运于无形之中,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理也。天岂谆谆然有物以命之乎?远求前古未之或闻,下验庶民无所取信。而王旦乃以龙图授羲龟书錫禹比之,使帝之精诚一寓于非,所寓可胜惜哉。”(P680)正因为罗氏的正统儒家思想,他不赞同封禅,认为“不以尧舜三代之君为法者,皆妄作也。”(P680)
面对宋金对峙,民族斗争激化,他主张谨慎进行战争。认为“师旅之兴必有谓”,后世“有和戎克定之说”不足尚,“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诗曰:‘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是也,及其为中国患也,則亦驱之出境而已。’……此圣人之格言,万世不易之理也。(P696—697)
罗从彦主张依照“祖宗故事”行事,他批评王安石“变更祖宗法度,创为新说”,(P 706)主张恪守祖宗之法。他说:“自英庙以至神宗之初,光每与吕诲同论祖宗之制,盖惩于此矣。王安石用事,又复启之,蔡京恃以为奸,其权大盛。天下之士争出其门,根株蟠结,牢不可破,遂为腹心,痼疾可胜言哉。今则祖宗之法具在,但守之勿失,推之万世,虽至于无穷可也。”(P713)罗从彦也能比较辨证地看待王安石变法,如他批评司马光的议论之失,不知“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P716)“去元丰间人与罢免役二者”也是失误之处。(P716)同时罗从彦还批评王安石伤于太刻。(P725—726)
三
《遵尧录》反映了罗从彦以“祖宗故事”为当政者提供统治经验的想法,主张遵守“祖宗法度”,反对纷乱的政局。意在纠正王安石变法后带来的政治不稳定与社会动荡,从而面对金朝的威胁。他所举出的“祖宗故事”明君贤臣事迹,主要是用儒家的价值观判断的,也就是说要确立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
徽宗时代北宋内忧外患严重,罗从彦居乡授徒,传播道学。然而他位卑未敢忘国,“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上书建言,体现出士人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后人评论《遵尧录》说:“大抵以我国家一祖开基,列圣继统,纲正目举,无汉唐杂霸之未醇;君圣臣贤,若舜禹遵堯而不变。备述太宗凡边防事机之重,尽守规模,复言仁祖承封祀宫室之余,益加恭俭,揄扬丕宪,推本深仁。大而郊庙宫掖之严,次而朝廷郡国之政,或释言以极发明之旨,或辨微以寓讽谏之诚,末陈元丰间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作俑之过,管心鞅法,创为功利之图,章倡蔡隨,浸兆裔夷之侮。”(P761)虽然罗从彦的主张在当时未被采纳,但是作为思想史的资料却长存世间,他的痛心疾首之言,无愧于其生活的时代。

常建华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生,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学博士。主攻中国社会史、明清史。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交换研究员,1994.4-1995.4)、韩国汉城大学(特别研究员,2001.8-2002.8)以及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访问学人,2002.12)进行学术研究与访问。担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2000年成立以来)、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91年以来),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暨秘书长。著有《宗族志》(1998)等著作,1984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及杂著百余篇。招收中国社会史、明清史方向的研究生。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