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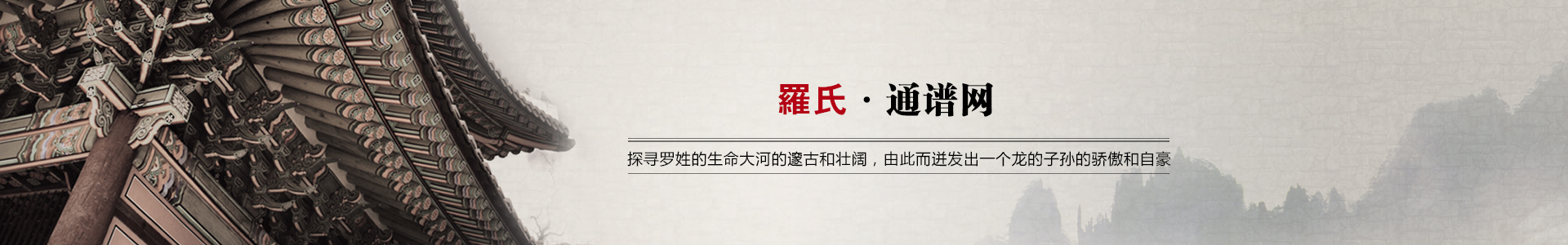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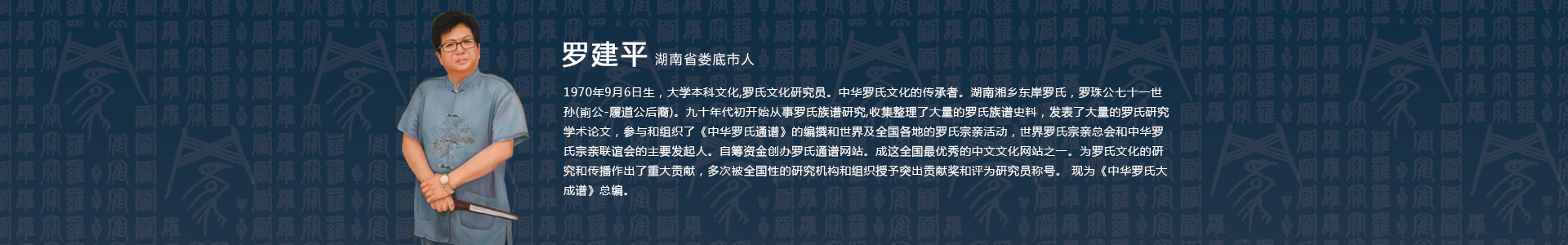
湖南最早的哲学家罗含
陶用舒 发布时间:2008-05-02
李商隐在关于十二星座的组诗《菊》中说:“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将晋代两位著名的文化人相提并论,陶渊明主要活动于东晋末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诗人,堪称一代诗风的开创者。罗含则活动于东晋早期,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堪称湖南的第一个哲学家。陶渊明出身低微,其思想与艺术风格和当时的文人倾向相背,故在当时为人所轻。但是,从唐朝开始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对中国诗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至今,对陶渊明的研究仍是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罗含出身世家大族,官运亨通,对当时社会、特别是思想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但是,其后却似乎为人所轻,被学术界忘记了,著作散失,声名不显。至今,对罗含的研究仍几乎无人问津。
晋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时期。西晋统一之初,政治清明,生气勃勃,人心思安,发奋生产,曾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繁荣时期。当时,湖南建置基本上承袭东吴,仍属荆州,境内有八个郡:武陵、天门、长沙、衡阳、湘东、零陵、桂阳、邵陵。经济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牛耕普遍推行,生产技术提高,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秩序安定。但是,随着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爆发和加深,由动荡、叛乱而战争,终于导致了中国长期分裂,政局动荡,战争频繁,经济破坏,人民逃亡。在大动乱的环境下,一方面加深了广大人民的痛苦与灾难;另一方面,则在迁徙流亡中,加强了全国各地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交流、融合,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日益发展壮大。湖南人民也更多地接触到了中原、北方等地区较为先进的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从而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两晋王朝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门阀世族的形成,并操纵着国家政治和经济。门阀世族,或说世家豪族,是中国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地主阶级中享有高贵身份的等级,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特殊产物。最早出现于东汉末期,他们世居高官显贵,或世代儒门。其后,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更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两晋南北朝时期,湖南最大、最知名的门阀世族,是欧阳世家,代表人物为欧阳,史称欧阳一家“合门显贵,名振南土”。罗含也是湖南世族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曾祖父罗彦为临安太守,父亲罗绥为荥阳太守。湖南世族多习儒业,不乏有成就的学问家、文学家。罗含就是其中著名的学者,所著文章刊行于世”,其中,《更生论》是古代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被称为“括囊变化,穷极聚散”的好书。《湘中记》则是一部有价值的地理学著作。
罗含(公元293—369年),字君长,号富和,桂阳郡耒阳人。幼年丧亲,为叔母朱氏抚养成人。好学勤读,博学能文,不慕荣利,志尚高远。荆州刺史曾三次召他为官,均辞谢不就。后杨羡任荆州将,慕其才学,引荐他为主簿,亦再三推辞。杨羡为江西新干人,罗含之父曾任该县知县,在杨羡坚请下,罗含方才就任。不久,调任郡功曹刺史。成帝威和九年(公元334年),罗含四十一岁,荆州刺史庾亮引为江夏从事。罗与江夏太守谢尚友善,谢尚器重罗含的才华,称之为“湘中之琳琅”,迁荆州主簿。次年,桓温任荆州刺史,任罗含为征西参军,后转任荆州副驾。桓温为控制全荆州,排挤谢尚势力,特派罗含到江夏检劾谢尚。罗含则巧妙地调和桓、谢关系,缓和矛盾。罗含又在城西小洲上建茅屋数椽,伐木为床,编苇作席,布衣蔬食,安然自得。其气度才华,更为桓温所重视。穆帝升平四年(公元360年),罗含任郎中令。稍后,朝廷又召罗含入都为正员郎,擢升为散骑常侍、侍中、廷尉,转调长沙相。其时,桓温伐燕失败,罗含乃着力调整桓温与朝廷的关系。其后,罗含年老辞官归里,加中散大夫。晋废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罗含病逝,终年七十七岁。
罗含是颇有成就的思想家、哲学家、地理学家。其中,《更生论》是其代表作,它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规律及其性质,是古代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全文如下: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总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谈,今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寻诸旧论,亦云:‘万兆悬定,群生代谢。’圣人作《易》,已备其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苟神可穷,有形者不得无数。是则,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我无穷之涂;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与运泯复,不成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又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质有聚散,往复之势也。人物变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复有常物。散虽混淆,聚不或乱,其往弥远。故其复弥近。又,神质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离。而莫慰离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识散之必聚。未之思也,岂远乎哉者?凡今生之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于体无所厝,其意与已,冥各不自觉,孰云觉之哉?今谈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达观者所以齐死生,亦云死生为寤寐。诚哉是言。”(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更生论》全文仅392个字,但内容和意义都十分深刻:
第一,指出天是万物之总和。
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所谓“玄学”,是指研究《老子》、《庄子》、《周易》三本书的学问,称之为“三玄”。王弼(公元226—249年)在《老子注》中说:“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也即“虚无”。天地万物,就是这种“虚无”所派生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宣传“天生(众)民而树之君”,强调君主是由天命决定,派来统治人民的。故这种学说的目的,在于宣传“虚无”,承认天命,取消斗争,服从命运,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罗含指出:“天者何?万物之总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强调天是万物之和,而不是“虚无”,是一种可以感知的物质。人也是天中一物,从而肯定了人民的地位。在当时,承认天是物质的,人是天中一物,是一种大胆的、进步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罗含著《更生论》,则用当时流行的玄学崇有思想,论证人死更生,谓“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他以神、形质为对偶关系,对偶分离,身死神在。而散必有聚,到头来形神还会再结合,形成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其实便是旧的生命,“凡今生之生,为即昔生”,“今谈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抹杀了前世今生的区别。这种崇有论的神不灭论,离佛家轮回说的本意更远。罗含同时代人孙盛,即就《更生论》提出相反意见:“吾谓形既粉碎,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弘明集》卷五)从“万物一理”的一元论角度,论证形体既死,知觉也会跟着化为异物,不能回复旧观。
第二,强调宇宙万物是发展变化的、即“更生”。
“宇宙”即宇宙万物的总称。“物”,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即精神凌驾于物之上,而且物是静止不动、永远不变的。罗含认为:“今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这一段话意义深刻,他提出了“天地”和“万物”两个概念,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的关系。一是说“万物有数,天地无穷”,即认为“天地”是根本、是本原、是主体,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很流行的观点。二是说“天地无穷,出于万物”,即“天地”的存在,要依靠“万物”的存在。如果没有“万物”,则“天地”也就不存在了。实际上这是对前一点“万物有数,天地无穷”的否定,而肯定“万物”是根本,是本原,是主体。这是非常大胆的对“天地永存论”的挑战,对“天地”无上权威的否定。三是说“万物更生,天地无穷”,所谓“更生”,即重新获得生命。司马迁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里是说:万事万物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不断地死亡(有终),又不断地新生(更生)。只有万事万物的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更生,天地才能无穷、才能无终。这里关于万物更生的思想,即万事万物不断发展、变化、新生的观点,是辩证法思想的体现,是罗含哲学思想的闪光之处。
第三,认为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
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是否有规律可循?唯物主义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如春夏秋冬的依次更替,昼夜的循环,生物体的新陈代谢。唯心主义否认这种规律,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来源于神秘力量,如“天命”之类。罗含的观点趋同于前者,他说:“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我无穷之涂;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所谓“定数”,本是迷信语言,所谓“荣悴有定数,天命有志极。”(刘峻:《辨命论》)作一定、必然解。罗含认为人和自然万物都有一定的质的规律性,都有其特定的成分,它们之间的变化、“更生”,也是有规律的,“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而不是混杂无章的。
第四,认为万事万物的变化只是形式上的变化。
在事物变化的问题上,同样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斯大林说:“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对此,罗含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提出“更生”的观念,承认万事万物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万事万物的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不是本质的变化。他说:“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已别矣。”又说:“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即是说:天地虽然无穷大,但其秩序是清楚的;事物虽有千种万种,但质的区别始终是存在的。因此,罗含认为万事万物的变,不是本质的变化,只是形式的变化、表面的变化。即:有与无、我与彼,不能转化,事物只是“聚散隐显”,不断地改改其形式。实质上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变化观。
把这种形而上学的变化观运用于分析当时的现实社会,罗含提出:“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又说:“今我故昔我耳。”意思是说:门阀世族,传自祖先,其地位不会变动,世族永远是世族;而寒门、佃客、奴仆,也永远是寒门、佃客、奴仆,不可能易位。“今我”是“昔我”的翻版,外形虽然变化,但内质是一样的。显然,这是为门阀世族服务的哲学。罗含的这种观点,当时曾受到长沙太守孙盛的批评。孙盛写信给罗含,首先肯定《更生论》“括囊变化,穷寻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辞致亦快。是好论也”。同时批评说:“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浑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强调变化会产生“异物”,世族和寒门、佃客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帝王将相也可能在寒门、佃客中产生。从罗含给孙盛的回信看,并没有接受孙盛的意见。罗含虽然承认“化者各自得”,但又强调“其所化颓者,亦不失其旧体”(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不失旧体”,即原来本质的东西不会失去,始终存在。可见,罗含未能跳出形而上学的怪圈。
第五,关于“神不灭”的观点。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佛教所宣传的“神不灭”论,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神不灭”,就是灵魂不灭。即是说:一个人今生的富贵贫贱,都是前生决定了的;所以对今生的遭遇,只能接受,只能忍受;好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来生。显然,罗含也受到佛教“神不灭”思潮的影响。他根据《周易》提出:“穷神知化,穷理尽性”,作为“神不灭”的经典理论。认为“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质有聚散,往复之势也。人物变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复有常物。散虽混淆,聚不或乱。其往弥远。故其复弥近。又,神质冥期,符契自合。”强调“神”与形体是“自然的偶合”,形体虽然可以“粉散”,但“有其往”,“复有常”,在冥冥中又能“聚合”,似有“符契”。实质上,这是“神、形可分可合”的唯心主义观点,即人的精神(灵魂)和身体可以结合,也可以分开。对此,一百多年之后的范缜,在《神灭论》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由此提出了“神形合一”的原则,强调“形”即“神”,“神”即“形”;“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是实质,“神”由“形”产生,“神”、“形”不可分,即精神物质不可分。
第六,预言中国必定由分裂走向统一。
罗含关于“神不灭”、“神形可分”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时,却提出社会有分裂、就会有统一的辩证观点。他说:“世皆悲合之必离。而莫慰离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识散之必聚。未之思也,岂远乎哉者?”所谓“离”、“散”,就是社会的分裂局面,“合”、“聚”,就是社会的统一局面。罗含的这种观点和预言,反映了当时人民迫切希望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良好愿望,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同时,这种观点也符合辩证法的思想原则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
综上所述,罗含的《更生论》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更生论》的基本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包含着唯物论的因素。特别是在《更生论》的言论中,有不少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不承认天命,肯定事物的发展变化,期望统一,都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除《更生论》外,罗含还著有《湘中记》三卷,又名《湘中山水记》。显然,这是一部关于湖南地理的著作。罗含生长在湖南,又长期在湖南地区为官和活动,经常察访民情,考证地理,时有所得,当有妙论传世。
(作者系湖南城市学院教授)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